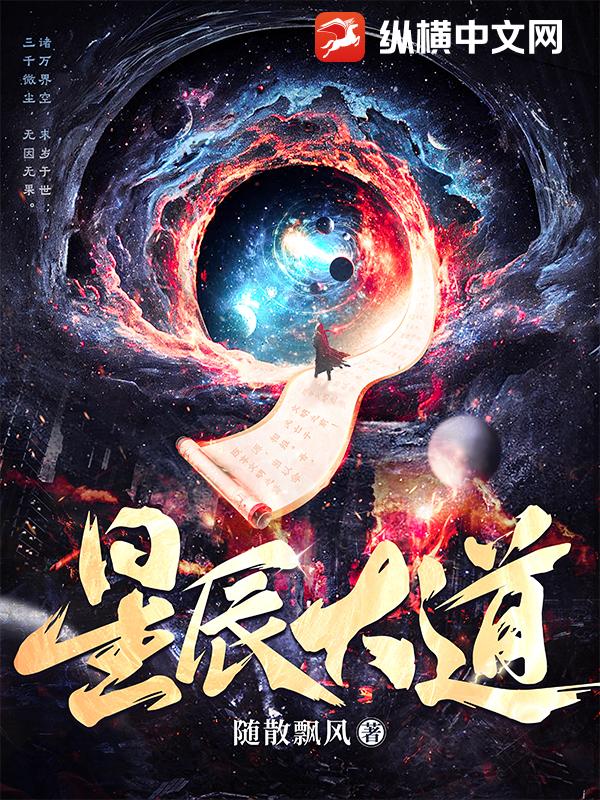沈少烜将鎏金怀表按在青瓷枕凹陷处时,枕芯突然传出机括转动的脆响。三年前沈家灭门那夜,爷爷就是抱着这只景德镇御窑青瓷枕,在苏州河码头被乱枪打成了筛子。
"沈少爷当真要开这血玉镯的煞?"白露的丹蔻指甲划过我掌心,她旗袍立领下隐约露出半枚铜钱大的烫痕——和父亲账本里夹着的当票拓印一模一样。昨夜她在百乐门唱《天涯歌女》时,我亲眼看见章大帅的副官往她坤包里塞了把勃朗宁。
马六蹲在雕花门廊下磨刀,刀刃在石板上刮出带血的碎屑。这个哑巴车夫是唯一从沈家火场爬出来的活口,他脖颈的烧伤疤里嵌着半块血玉镯残片,此刻正与我手中这枚玉镯的缺口严丝合缝。
"民国六年,沈老太爷用二十船桐油换的可不是普通镯子。"我旋开玉镯内侧暗格,磷粉绘制的星图突然在月光下显形,"关外张作霖的军师说过,这镯子里锁着渤海国的长生祭坛。"
白露忽然用簪子挑破自己指尖,血珠滴在玉镯夔龙纹上竟发出婴儿啼哭。鎏金怀表的指针开始逆时针疯转,青瓷枕底突然弹出一卷帛书——那是爷爷用契丹文写的《渡亡经》,最后一页黏着半张仁济医院的出生证明,产妇姓名栏赫然写着白露的本名:沈秋棠。
"你后腰的胎记,"我扯开她旗袍后襟,三道爪痕状的青斑在烛光下泛着磷光,"和沈家祠堂壁画里的渤海国巫女一模一样。"
马六突然暴起,砍刀劈碎窗棂的瞬间,章大帅的兵痞正从院墙翻进来。白露腕间的血玉镯迸出刺目红光,最先闯入的士兵突然七窍流血——他们太阳穴上都插着刻满梵文的银针,和三天前死在沈家当铺的十七个典当行伙计伤处相同。
苏州河底渗出的黑水漫过脚踝时,马六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半块发霉的绿豆糕,夹着张泛黄的妓院流水单——醉仙楼头牌海棠的恩客名录上,章大帅的化名与爷爷的私章并列在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七月十四。
"令祖用沈家七十二间当铺做局,把渤海国的阴阳棺从长白山运到上海滩。"白露将玉镯浸入河水,镯身裂纹里突然游出无数发光血虫,"知道为什么选中七月半?那天鬼门关的守夜人,正是你们沈家祖上供奉的洞冥鬼王。"
水幕轰然升起,河底显出座倒悬的青铜城楼。我们穿过刻满人面鱼的牌坊时,马六突然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他的瞳孔变成诡异的竖瞳,指甲暴长三寸,生生撕开了迎面扑来的鲛人守卫。
"你喂他吃了沈家的续命蛊?"我攥紧帛书后退半步,白露却将染血的簪子插进自己锁骨,"少烜还不明白?三年前被烧死的三百二十七口人,不过是给长生祭坛开的生桩。"
祭坛中央的琉璃棺里,躺着个穿明黄道袍的童尸。当我看清童尸左手缺失的小指时,浑身血液瞬间凝固——那截断指正戴在我贴身二十年的银戒里,戒面暗纹与玉镯内侧的契丹文完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