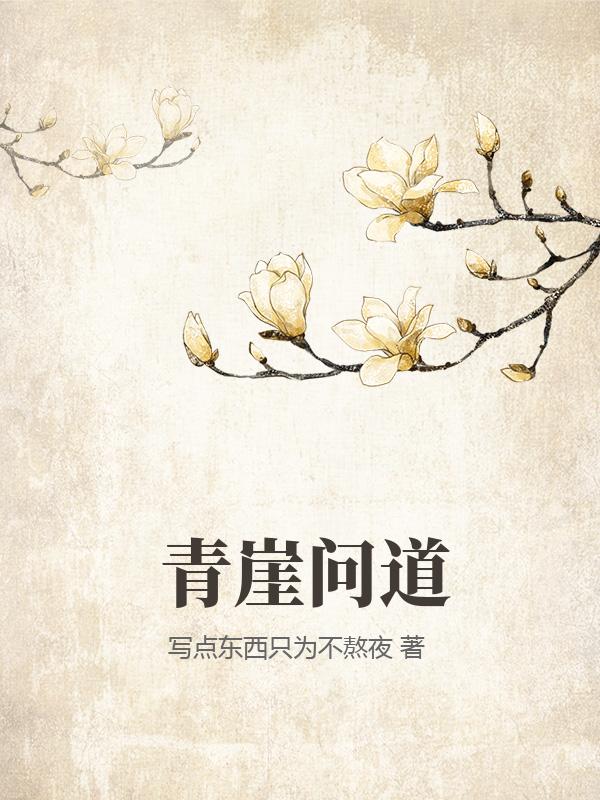陆青崖蜷缩在矿洞最底层的裂隙里,指甲深深抠进岩壁。玄铁砂的碎屑混着血水从指缝间渗出,在幽蓝的磷火下泛着铁锈般的暗红。三百丈深的矿脉像条吞骨的巨蛇,每一次呼吸都绞得他肺叶生疼。矿洞顶上渗下的水珠砸在肩头,寒意刺骨,却浇不灭脊背上烧灼般的痛楚——那是玄铁砂淬体留下的烙印,青鳞纹如活物般在皮肤下游走,每刻下一道痕,便离锻体三阶近一分。
磷火在穹顶结成蛛网,映得岩壁上血字斑驳。那些是历代矿工用镐尖刻下的遗言:"悔入玄天""葬骨处""九重渊下无轮回"。陆青崖的视线扫过这些字迹,喉头动了动。三日前,他刚被扔进这矿洞时,曾摸到一处未干的血字,指腹下是陈二狗歪扭的字迹——"香囊在左三脉"。那时血迹尚温,他以为这只是陈二狗又一次醉酒后的疯话,直到昨夜在污水潭边捡到那半片浸血的香囊。香囊上的紫藤花纹已被血污浸透,丝线却诡异地泛着磷光,仿佛在指引什么。
"叮——"镐尖撞上岩层的闷响在甬道里荡开,几点火星溅在他裸露的脊背上。那些火星没有熄灭,反而顺着青鳞纹的沟壑游走,烧出蛛网般的焦痕。这是玄天宗外门弟子入矿洞的第三日,也是他锻体一阶突破的生死关。陆青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舌尖尝到血锈味。矿洞深处的风声裹着断续的呜咽,像是陈二狗失踪前最后的呻吟。那声音里混杂着铁链拖地的摩擦声,还有某种黏稠液体滴落的回响。
三日前,陈二狗还拍着他的肩膀大笑:"青崖,等攒够贡献点换了《锻骨诀》,老子一拳能轰穿这破矿!"那笑声震得矿壁簌簌落砂,惊飞一群血眼蝙蝠。陈二狗总说自己的拳头比玄铁硬,他曾一拳砸碎过三寸厚的青岗岩,指节上的老茧厚得像铁甲。那年冬雪压垮了陈家的茅屋,女儿小满咳出的血染红了半片枕头。陈二狗跪在雪地里剜出自己一块腿骨,换来三颗续命丹。"爹不疼,吃了药就好…"他哆嗦着把丹药塞进女儿嘴里,却不知那丹药是用魔种幼虫炼的。小满服下续命丹的第三日,青鳞纹爬满了她的脖颈。陈二狗抱着女儿蜷缩在破庙角落,听着她胸腔里传出金属刮擦声。子夜时分,小满突然睁开眼,瞳孔已化为晶紫色:"爹爹,我好饿…"她一口咬住陈二狗的右臂,生生撕下块血肉。陈二狗没有躲。他看着女儿吞下血肉后皮肤玉化,背后凸起根根骨刺。当玄天宗修士破门而入时,小满已化作半人半妖的怪物,指尖滴落的毒液腐蚀着地砖。为首的修士掷出锁链贯穿她的心脏:"魔种成熟体,带回宗门炼剑!"陈二狗疯了一般扑上去,却被一脚踹断三根肋骨。他永远记得小满被拖走时的眼神——那双紫晶瞳孔里,还残存着女儿的一丝清明。
可昨夜收工时,他的镐头孤零零插在岩缝里,粗麻布袋空荡荡的,唯余半片绣着紫藤的香囊——那是他凡间妻子的信物。香囊浸在污水里,丝线泛着诡异的紫光,像是某种活物的触须在水中扭动。陆青崖记得,陈二狗的妻子是个绣娘,临别时在香囊里缝进了女儿的胎发,说是能辟邪。可如今这香囊的紫线却如毒蛇般游走,透着不祥。
陆青崖摸向怀中那半片香囊。指尖刚触到湿润的布料,矿洞另一头突然传来铁链拖地的哗啦声。污水潭咕嘟冒泡,浮起半张被玄铁砂填满眼球的人脸。那面孔随波纹漾开诡异的笑,下颌骨突然张开,喷出一股紫烟。陆青崖翻身滚开,紫烟触及岩壁的瞬间,青石竟生出肉瘤般的增生。这是"瘴妖"——玄天宗用来清理废矿的毒物,沾之则血肉晶化。三日前,陈二狗就是为了救他,徒手捏爆了一只瘴妖,掌心至今留着焦黑的灼痕。那日瘴妖的紫烟几乎触及陆青崖的咽喉,陈二狗却赤手撕开那怪物的胸腔,挖出一颗跳动着的紫色晶核。紫色晶核在陆青崖掌心剧烈震颤,表面血管状纹路突然暴起,扎入他的血肉。剧痛中,他看见晶核核心的黑影膨胀成婴儿大小,生出八条蜘蛛般的节肢。"快走!"陈二狗吼着,掌心被腐蚀得白骨森森,却硬生生将晶核捏成齑粉。"吃掉它!"陈二狗的吼声混着血沫。陆青崖发狠咬破舌尖,精血喷在晶核上。那黑影发出凄厉尖啸,节肢疯狂撕扯他的腕骨。就在此时,陈二狗残破的身躯突然暴起,用最后一丝力气捏碎晶核。黑血喷溅,陆青崖右臂青鳞纹瞬间转为暗红。他眼睁睁看着陈二狗的尸体在血泊中晶化,最终碎成满地紫砂。砂粒汇聚成箭头形状,直指矿脉深处——那是陈二狗用命换来的生路。
"戌时三刻!交砂!"王监工的吼声裹着鞭影劈下来。陆青崖猛地低头,鞭梢擦着耳际掠过,在岩壁上抽出一道半尺深的裂痕。他死死攥住腰间粗麻布袋——里面躺着今日挖到的七两玄铁砂,离宗门规定的十两还差三成。矿洞另一头传来惨叫,一个佝偻的身影被拖向血镐渊,脚踝在岩石上拖出蜿蜒的血痕。那是个头发花白的老矿工,昨日还教过陆青崖辨识含砂量高的"龙鳞岩"。老人布满裂口的指尖曾点在他掌心:"瞧这纹路,像龙鳞吧?这种石头一镐下去,能崩出三两砂!"此刻那双手无力地垂着,指甲缝里塞满紫黑色的血垢。老人的嘴唇翕动着,似乎在重复某个名字,却被监工的咒骂声淹没。
"陈二狗昨日交了多少?"王监工靴底碾着他的指节,腐肉味混着酒气喷在脸上。"十…十二两。""砰!"布袋被一脚踢飞,砂粒泼洒在污水里。陆青崖盯着那些闪烁的蓝点,突然发现其中有颗砂砾泛着诡异的紫芒。那紫光如活物般蠕动,顺着污水爬向他的指尖。他想起陈二狗香囊上的紫线——同样的色泽,同样的不详。三年前的雨夜,陈二狗抱着高烧的女儿跪在山门前,守门弟子弹指将香囊烧成灰烬:"凡尘孽障也配入仙门?"那香囊是他妻子熬了三宿绣的,紫藤花瓣里藏着女儿胎发。此刻污水中的香囊残片突然颤动,紫光如蛛丝缠上陆青崖手腕。他感到一阵刺痛,仿佛有无数细针顺着血管扎入心脏。
后颈突然传来针刺般的剧痛。蛰伏三日的魔种顺着脊椎窜上颅顶,青鳞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尾椎向上蔓延,所过之处皮肉寸寸晶化。王监工暴退三步,鞭柄上镶嵌的窥灵玉炸成齑粉:"魔种暴动!快禀告戒律堂!"
陆青崖的视野开始扭曲。污水里的紫砂腾空而起,在他掌心凝成一道剑形虚影。这是《太虚剑经》记载的护体剑罡,本该筑基期才能施展的秘术。剑光扫过之处,岩壁上的青苔瞬间石化,监工腰间的传讯符箓还未燃尽就化作飞灰。他听见自己肋骨折断的脆响,魔种在吞噬剑罡反哺的能量,青鳞覆盖率从15%暴涨到45%。青鳞纹爬过锁骨时,陆青崖听到识海中响起金属刮擦声。那是三百年前被镇压在此的剑魔残魂,正透过魔种窥视他的灵台:"小子,你的剑骨比初代宗主更纯粹……可惜要便宜噬道者了。"鳞片覆盖处传来万蚁噬咬的痒,接着是彻骨寒——晶化的皮肉正在剥离,露出玉质骨骼。他低头看去,右臂已完全化为青玉般的质地,指尖轻轻一划,便在玄铁岩上留下深痕。
矿洞深处传来龙吟般的震颤。玉佩在胃里灼烧的第三天,陆青崖开始咳血。血珠落地竟凝成剑形,将青石地砖斩出裂痕。玄天宗修士发现异样,将他拖进洗髓池逼问:"说!林素心把《太虚剑经》藏哪了?"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娘亲的真名。池水灌入鼻腔时,他看见娘亲被铁链悬在祭坛上,胸口插着七柄噬魂钉。她的血顺着锁链流入地脉,在矿洞深处汇聚成血池。"青崖…活下去…"娘亲最后的神识刺入他识海,玉佩应声碎裂。无数金色符文从胃里涌出,在他脊背上刻下《太虚剑经》第一卷。当晚,看守他的三名修士离奇暴毙,尸体上布满剑痕。
怀中的残破玉佩突然发烫,烫得他胸口皮肉焦黑——那是娘亲临终前塞进他襁褓的物件,此刻竟浮现出蜿蜒的纹路。西三道矿脉的地图在识海中一闪而逝,无数光点指向某处沸腾的血池。十二道诛魔剑光结成"天罗地网",剑鸣震得矿洞簌簌落石。为首的戒律堂弟子掐诀冷笑:"锻体期也敢染指《太虚剑经》?"剑网收缩的刹那,陆青崖的晶化右臂突然暴涨,五指插入岩缝生生撕下一块"龙鳞岩"。玄铁砂洪流倒卷,裹着他撞向第三条矿脉的封印石。
石屑纷飞间,陆青崖看清裂缝中的骸骨——不仅颈椎生着青鳞纹,胸骨更是完全玉化。断裂的剑刃插在颅骨上,剑柄"太虚"二字被血垢覆盖。骸骨指骨间攥着半卷《锻骨诀》,那是陈二狗梦寐以求的功法。当黑血顺伤口渗入时,他忽然明白:所有矿工都是玄天宗的"剑骨培养皿"。这些被青鳞纹侵蚀的躯体,不过是用来培育剑骨的容器。封印石炸开的瞬间,血池沸腾如活物。骸骨手中的断剑嗡鸣,竟与陆青崖的剑罡共鸣。青鳞纹转为暗金,魔种在他识海中狂笑:"这才对!用你的剑骨吞了这池血精!"
戒律堂长老的威压碾碎洞顶巨石,陆青崖却迎着威压跃入血池。污血灌入口鼻的刹那,他看见池底躺着数十具玉化骸骨——每具骸骨颈间都挂着残破玉佩,与他娘亲留的那枚一模一样。那些玉佩拼凑起来,隐约能看出"太虚"二字的轮廓。血池底部比陆青崖想象的更诡谲。玉化骸骨并非静止,它们的指节仍在微微颤动,仿佛被某种力量驱使着重复生前最后的活动——挖矿、挥镐、挣扎。当他游近中央玉碑时,骸骨们突然齐齐转头。数千具骷髅张开下颌,发出金石相击般的嘶吼:"甲子七九…归位…"声浪震得血池沸腾,池底裂开九道缝隙,伸出布满倒刺的青铜锁链缠住他的四肢。玉碑背面浮现出血色铭文:"剑骨大成者,当为噬道剑鞘。以三千矿工之魂养剑,以剑骨之躯承魔。"碑文下方嵌着枚眼珠大小的血色晶石,正是陈二狗当年捏碎的瘴妖晶核放大万倍的形态。陆青崖的右臂不受控制地按上晶石。青鳞纹瞬间蔓延全身,与碑文产生共鸣。他看见三百年前的画面:娘亲林素心带领矿工暴动,却被凌沧溟镇压。她的剑骨被生生抽出,炼成困龙匣核心。而那些暴动者的亡魂,被封印在血池永世哀嚎。"原来我也是实验体…"陆青崖嘶吼着扯断锁链。血池疯狂翻涌,骸骨们纷纷爬起,将残存剑意注入他的剑罡。这一刻,他既是剑骨,也是剑。
陈二狗的香囊残片在血水中燃烧,紫光勾勒出西三道矿脉的全貌。那些蜿蜒的矿脉根本不是天然形成,而是巨型剑阵的刻痕。陆青崖的剑罡突然暴涨三倍,不是靠灵力,而是无数剑骨残魂的嘶吼。那些魂魄在血池中挣扎了三百年,此刻终于找到宣泄的出口。
当最后一缕剑罡消散时,他倒在血泊中,耳畔是戒律堂长老的怒吼:"又是剑骨反噬!把这废物扔进洗髓池!"怀中的香囊残片已化为灰烬,唯有岩壁剑痕在血光中明灭,仿佛在书写新的谶语。矿洞深处传来悠长的龙吟,初代宗主的残魂在剑冢深处苏醒,而三百丈之上的玄天宗正殿,掌门凌沧溟抚摸着困龙匣上的裂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匣中封印的魔剑震颤不止,剑身上的血纹正与陆青崖颈间的青鳞纹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