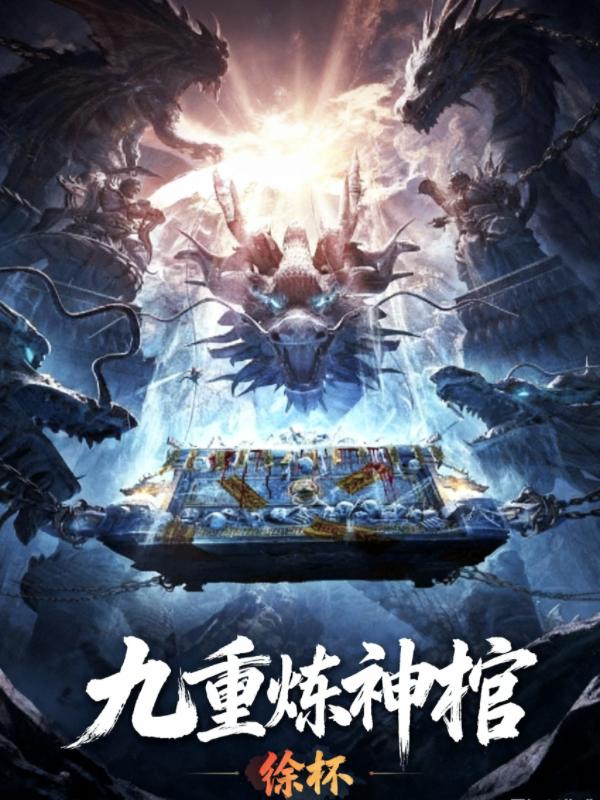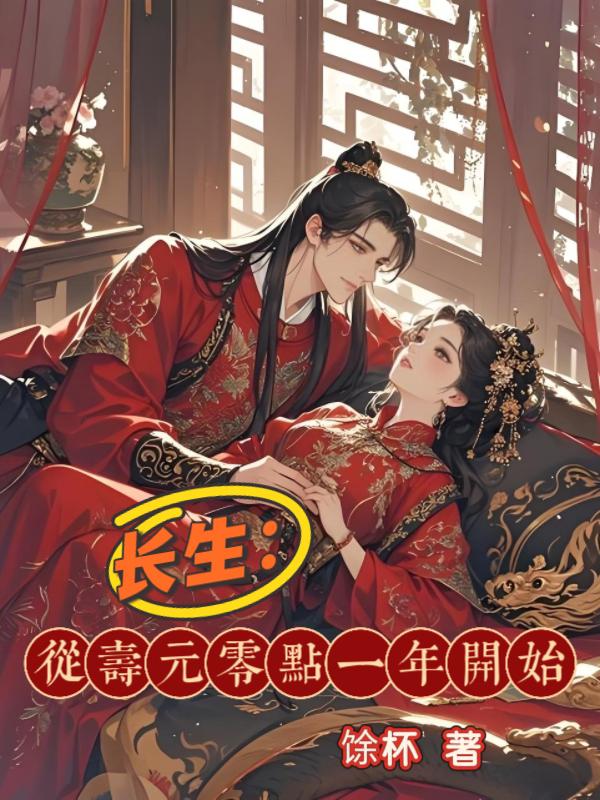卫鉴虽然已经是高手了,可高手也需要睡觉。
每日在“卫鉴”与“卫建国”之间切换,现代与古代之间,仿佛都没有睡觉和休息,按理说应该是疲惫异常。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每次醒来,感觉睡眠都很充足,想了很久都没想通,他准备等周末约个学医的朋友,出来问问。
今天正要睡下时,老杨头找他单独说话。
“卫鉴,你的功夫已很好了,不遇到绝顶高手的话足够自保。”
“老杨头,你不对劲。”
“别没大没小,哪不对劲?”
“我平时就这么叫的.....你从来没说啥,还有,你平时说话不这样。”
“平时我什么样?”
“很猥琐,你平时....”还未说完,卫鉴剩下的话,被一巴掌拍在脑袋上,生生打断。
老杨头今天确实不一样了,渊渟岳峙,一派宗师气度。打断了卫鉴的话语之后,也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
“杨宗师。”卫鉴只得开腔,换了个称呼,“你记忆恢复了?”
“恢复了一些,那天见到韩三的后人,想起一些事。”
“那你以后什么打算,是回家团聚还是......”
老杨摇了摇头,交待卫鉴继续修习给他的那份拳谱和九真上书后就要走。
“别走啊老杨头,你这岁数了,能回得了家吗?”一着急,卫鉴又顺口叫出了原来的称呼。
老杨又摇头,“我哪也不去,跟你一并先去临安,你若愿意陪我去南海了,就告诉我,我就在附近,先恢复下内伤。”
“你何时受的伤,需要药么?”
“很多年前了,我以前的记忆残缺不全也是源于此。”
“老杨头,你是不是最近的记忆也丢了,我早把九真上书给全真教的牛鼻子了,哪还能修炼?”
.......
老杨头思索良久,才理顺了最近发生的事,然后又给了卫鉴一巴掌。
“以后不要带我去画舫。”
卫鉴心中大声叫屈,明明是你猥琐的看那些游船上的白嫩大腿,关我何事,再说,那日终南山下时也没真去啊。
又思索片刻,老杨头让卫鉴不必再想九真上书的事了,吩咐完就不见人了。
~~~~~~
金州离武当不远不近,一行人走走停停,六天才到达武当山。
看着高大雄伟的峰峦、奇峭幽邃的岩涧,张松溪的心情终于好了些。如果不是二师兄俞莲舟在山上坐镇,他甚至不愿引这帮人上山。
除了辛冲。
这孩子着实惹人喜爱,天资、德行、心性无一不佳。如果能稍微在说话上注意那么一点,就更好了。
其实,那个卫鉴如果能年轻十岁,张松溪也想引他入门,不过看他现下的样子,显然早有师承。
张松溪自嘲一笑,我武功兴许还不如他,想什么引他入门之类的话?
带众人安置好后没多久,张三丰竟然也带着俩徒弟回来了,比预计要早了两天。
老道精神显然不错,直走到复真观门口时还在嚷嚷着。
“远桥,你总说每次在山上,理那些俗务,耽误了修行,才越来越比不上莲舟,我看不然。”
“师傅请示下,弟子听着呢。”宋远桥的声音永远那么憨厚老实。
“你看你,修炼来修炼去,搞了个儿子出来,人家莲舟至今还是独善其身,能比吗?”听着这话,几个道士的脸盘子都扭到了一起,其他人是憋着笑,宋远桥是憋着哭。
卫鉴没想到,与张真人的见面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张三丰看上去并不老,白发都没几根,离远了看跟宋远桥像是同龄人,不知是他显得年轻还是宋远桥显得老。
卫鉴拉了拉张松溪的袖子,小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我师父确实和大师兄年岁相仿。”张松溪并不在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这帮弟子,有些是战乱孤儿,师傅年轻时就已在山上悟道,收纳了不少人,有些师兄弟的名字都还是师傅给起的。”
“张真人给张四侠起的这名字就极好。”卫鉴奉承道。
张松溪脸一黑,他最近甚至已经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脸黑太多次了。“我的名字是父母起的,二老还健在。”
一个马屁拍到马腿上,卫鉴悻悻低头。
止住了要出门迎接的弟子们,张三丰把目光投向卫鉴一行人。
张松溪一一介绍,待到要介绍水鬼时,张三丰露出笑容:“陈江小哥儿可还记得我,那年我去汉中时,你在做贩鱼的营生,那咸鱼上的盐比鱼肉还多,滋味难忘啊。”
陈江大喜:“张真人竟然吃过晚辈卖的鱼,我都不知,定是当时眼拙,错把神仙当了俗人。”
张三丰哈哈大笑,又指着罗氏说:“汝以后可多来,吾弟子多,但都不是迂腐俗人。”
艳鬼本来不想上这武当山,听了这话真倒是生了几分下次再来的心思。
又吩咐将辛家三口人安排好后,张三丰见四徒儿一双眼睛不停往那辛家少年的身上看,便含笑点头,却是什么都没说。只嘱咐弟子给卫鉴安排到原来老三的那间屋子,众人路途疲惫,也就散去各自休息了。
~~~~~~
卫鉴做客居住的这间屋子,与他人不同,这竟是张真人亲传弟子的住所,一个小院儿里,住着四徒弟张松溪、五徒弟殷利亨,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胖子。
院子内外风景极好,雾绕云缠,峰翠秀丽,人似行走在画中。
张松溪不明白师傅为什么让他安排卫鉴住在这,观内明明有客房空着,难不成是想收他做徒弟?一边想着师傅有何深意,一边换下身上的衣服,抬头看到辛冲探头在门外,拘谨的不肯进来。
满意。
张松溪对这个少年越来越满意,如此不骄不躁,明明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亲传弟子了,仍见不到一丝得意,在无人处也能克己守礼,着实不俗。
“你来找我?”张松溪一边说着,一边慈爱的伸手去摸辛冲的头。
“我找卫先生。”
伸出去的手在空中停顿了片刻,张松溪回手掸平刚刚没有弄好的领口。
“跟我来吧。”
走到卫鉴住的屋内,张松溪和辛冲看见卫鉴正撅着屁股,在墙角观察着什么,完全没有听见二人的敲门声。
辛冲抚颌片刻,眯着的眼睛骤然张开,恭恭敬敬的问到:“卫先生可是此刻有所得?”
卫鉴说话了,说了一句张松溪完全听不懂的话。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辛冲睁大的眼睛又重新眯上,露出思索神色,连眉头都拧在一起。这道理太深奥,自己想不明白。
张松溪服了。服这俩人,一路上,一个敢说一个敢信,到了武当山本以为有所收敛,结果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看着辛冲一点点将时间浪费在姓卫的身上,张四侠黯然神伤,我的道理就不好么?
诶?
卫鉴‘诶’了一声,抬起身来,问二人啥时候来的。
他刚才本来在思索,老杨头最近是什么情况,准备回去查查老年痴呆症该如何治疗。结果换鞋的时候,发现墙角有字,便趴在地上伸长脖子去看,忍不住读出声来,没想到被张老四听到了。
“回卫先生话,弟子才来。”
张松溪悲甚,你辛二郎能不能不要总学周围人讲话,我们平时跟师傅的说辞,你用在姓卫的身上干啥。
卫鉴点点头,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问张松溪:“张四侠,这屋子以前是谁住的?”
“是我三师兄的,他已逝世多年。”
看着洁净的屋子,卫鉴想到该是有人一直在打扫,复又追问:“你可听他说过这句话?”
“鸡变狗不变这句?”
“是奇变偶不变,你看看这字是不是你师兄写的?”
还未等张松溪低头去看,卫鉴听到砰砰声不断,一个胖大男子双手撑地,飞也似的进到屋内。
看完墙角字迹,胖大男子仍不起身,卫鉴这才发觉来人竟是个残废。
张松溪扶起来人坐到椅子上,向卫鉴解释道:“卫少侠,这是我三师兄家属张弘基。”
名叫张弘基的胖大男子向卫鉴致歉拱手,满脸悲伤无论如何都藏不住,一开口也是声音沙哑:“卫少侠,我没听弟弟说过这句话,这字迹也不是他的,你如何有此一问?”
卫鉴并未回答,而是反问道:“那这屋子,可还有别人住过?”
武当六侠里,俞莲舟武功最高,张松溪头脑最好,宋远桥年纪最大。此刻听卫鉴这么问,张松溪心念电转,从书架上抽出几封信件,也像卫鉴一样趴在地上,对照着两边的字迹。
“是嫂子的字迹!是嫂子的字迹!”
卫鉴从未见过张松溪如此失态,也未见过他如此热情,此刻还抓着自己双臂使劲摇晃,一直问着,卫兄何解,卫兄何解啊。
“是一道数学题,你们应该不懂。”
“无妨,卫兄讲,我们听。”张弘基的声音也是愈发焦急。
于是卫鉴开始讲起了奇数、偶数、函数、象限角相关的知识。
辛冲听不懂,但他大受震撼。搜肠刮肚,想要从那些年蹲在师塾窗外偷听来的文字里面,找到那么一两句,来夸赞卫先生,可却一句都想不起来。
张弘基和张松溪也从一开始的点头连连,慢慢眉头紧皱。
卫鉴停了下来,无奈问道:“听懂了吗?”
三个听讲的对视一眼,由最年长的张弘基开口:“先不说这些,卫兄可知道这与我弟之死有什么关联?”
一个数学问题能死人?过分了吧。卫鉴愕然,摇头不知。
“卫兄可认识吴秀?”张松溪追问。
吴秀。
卫鉴咀嚼着这个名字,这已是这个世界上,第二次有人这么问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