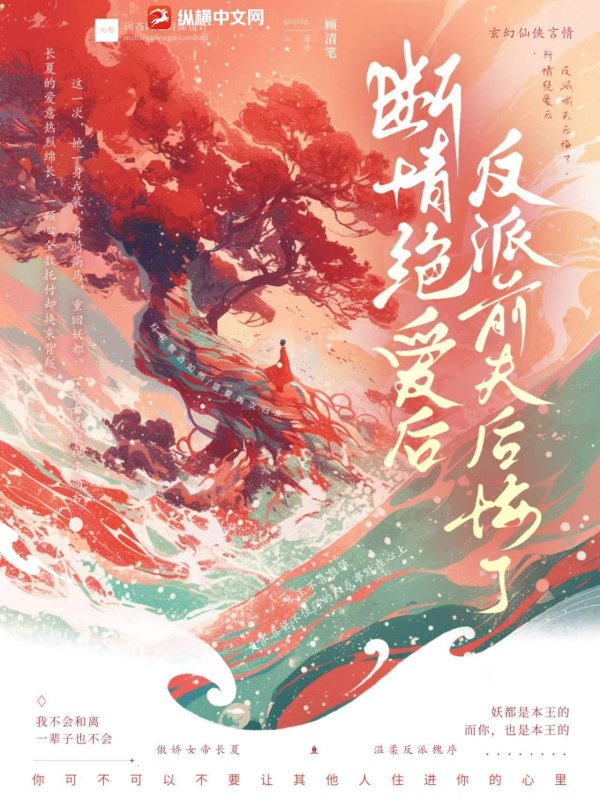一路上的难民依旧络绎不绝,白雪再次伴随着细雨缓缓落下。
阿辞牵着马,站在高山上,看着山谷绵延之中升起的袅袅硝烟,那些黑色的烟雾仿佛是一片白雪的唯一的颜色。
雪花夹杂着细雨落在她的身上,白雪淋头,赵扶桑自然地打开伞,朝着她靠了过来。
阿辞问道:“你可知阿寻他们去了何处?”
赵扶桑点点头:“那日我接到了巳宸大人的密信,来到关城外在一个小村之中找到了他们,瑞羽受伤了,阿寻和九和没事儿。”
阿辞点点头:“那便好。”
现在她也要找到他们了。
阿辞看着他手上的伤疤,眼眸顿了顿,接着当作没看见扭身走了。
赵扶桑赶忙跟上,将那斗笠蓑衣拿给她。
“你身子不好,还是先披上吧。”
现在阿辞虽然可以用灵力来让身体不受雨雪侵淋,但是不到关键时候,她还是不能如此。
她接过,赵扶桑则是轻车熟路地为她穿衣。
少年的眼眸在阿辞看不到的地方,里面的情绪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无尽的变化,他仿佛已经在心底暗暗下定了决心,那种想要将阿辞慢慢禁锢起来的暗色,让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问道:“阿辞,那日来找你的公子,是何人?”
阿辞抬眸看着他:“你有何事?”
赵扶桑微微低眸,将那些情绪掩藏起来:“看着他灵力好像十分高强,所以一问。”
阿辞这时说道:“你别想了,他可不收徒,而且把你交给他,我也不放心。”
赵扶桑却是听了一愣,抬眼时先是微微的讶异接着便是柔情和轻微的喜悦在双眸间化开。
“你不放心我?你是在担心我?”
阿辞看着他的眼中的笑意,甚是不解:“那又如何?有问题么?”
这小子的灵力至纯无比,若是被祭司的灵力侵蚀一番,那还得了。
就算不为这小子着想,起码也对为自己着想着想。
阿辞不顾他傻笑的神情,扭身牵马就走了。
赵扶桑还在心中暗自窃喜着。
失去情丝又如何,他还是以前的阿辞,他还在自己身边。
他呵呵笑着,赶紧跟上。
“阿辞,等等我。”
雪停了,两人紧赶慢赶来到了花锦城。
她坐在高马上,却迟迟不动,
她向赵扶桑伸手,赵扶桑会意了然将地图给她。
这花锦城和被西荒刚刚攻破的南岳城只隔着三江,以他的速度,若想迅速攻占炙汐域,那眼下只要相继再攻占花锦城和朔城即可。
这样下来,就直接到了妖都的腹地。
妖都危矣。
阿辞折起地图,接着问道:“你查的事情可有眉目了?”
赵扶桑回答道:“上一次巳宸大人查出了三王私下结交大臣,还圈矿山以练兵器,再加上私自贩卖军中兵器,致使栎阳城中士兵的那些兵器如同泥塑,死伤过万。妖尊得知大怒,将三王贬为庶民,关入地牢。这些事情本是你养伤期间发生的事情,可是就在一年后,西荒大军接连取下二城,妖尊以大局为重,让三王以庶民身份,戴罪立功,至于何时恢复他的爵位,并未说明。”
阿辞凝眉静静地听着赵扶桑的话,听到他说完后,她问道:“你何时知晓妖都王朝之事?”
赵扶桑也是坦诚地回答:“这些年,我总与巳宸大人互通信件,自然也是知晓了些。”
阿辞却是听懂了这话里面的意思,但也没有点破,只是对他说道:“你有你自己的去路,你若是想离开,不必和我说,自行离开去寻找新的出路即可。”
可是赵扶桑却是说道:“不,我不会离开的。”他不想每一次回来,阿辞都受伤,不想每一次回来都看见阿辞躺在血泊之中。
不省人事。
不愿意让阿辞每次都独自一人看着自己的背影离开。
就像那个人说的:赵家并没有赵扶桑。
阿辞听到他的话:“随便你。”
互通信件,恐怕是他师父在催着,让他尽快谋到好一点的官职,让他出去闯闯,跟着巳宸或许对他日后在官场当中会更有受益。
关城的事情,以及查出三王的事情他辅佐巳宸完成的不错。但如果他就这么回去辛衙所,说不定日后三王得知,他会连骨头都不剩。
但是跟着巳宸,有了执法司的名头,尽管三王使坏,也不敢怎么样。
这小子,竟然连这层都看不懂,真是个蠢货。
就在这时,阿辞拿起了一截白骨。
她靠近嘴边,接着轻轻一吹。
赵扶桑有些不解,但也没有过问太多。
阿辞放下后,便是开始等待,这时她又问道:“如今三王在何处?他的那些权力恐怕早就归于五王了吧?”
赵扶桑点点头:“三王如今驻守在哪里,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我们在寻找矿山的账簿时,确实有五王相助,那些案子结束后,五王也得到了些许的赏赐。”
阿辞眸色是几分邪气:这五王恐怕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把三王彻底扳倒,让他无翻身之日。让自己今后能有安枕之日。
这时风声掠过树影,阿辞下马,朝前走时,那漆黑的树影之下缓缓走出一个人来,那个人看到阿辞时身影先是一顿,接着是抬手拍了拍她的肩。
赵扶桑立即下马,跑了过去。
看清来者时,他松了口气,原来是瑞羽。
瑞羽十分欣慰地看了眼阿辞随后又看着赵扶桑。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看到了赵扶桑轻松一口气的样子,瑞羽回头看着周围:“怎么了?没有尾巴。”
赵扶桑摇摇头:“无事无事。”
阿辞这时问道:“城内情况如何?阿寻和九和呢?”
瑞羽这才说道:“我正要和你说,阿寻他们目前还是安全的,这是现在城中情况复杂,西岚军现在虽守着城池,但是却不得民心,而且将领之中有内讧出现。”
“内讧?”那此战岂不是必败无疑?
瑞羽这才说道:“城中共有两位将领,一个是元川途,一个听说是先王妃?”
赵扶桑疑惑地蹙眉:“先王妃?女子?”
瑞羽摇摇头:“不是,是个男的。”
在两人察觉不到的地方阿辞的眸色暗了几分。
她还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再次见面了。
赵扶桑疑惑地问:“男的怎么会是王妃呢?”
瑞羽用他打听到了小道消息回答:“这位王妃身份不一般,王爷的身份也不一般。听闻那位王爷是妖都第一位女王爷,权势滔天,二人成婚后,妖都突遭变故,王爷生死未明,王妃也就暂代王爷之职,算时间的话,也有五年之久了。”
阿辞冷笑一声:这些都是什么屁话。
只是赵扶桑还在沉默着,她微抬下颚对他说道:“你想什么呢?”
赵扶桑垂眸:“只是觉得王爷或许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一切被其他人占领拿走。”
阿辞听到,眉头轻轻一抬,顿时来了兴致:“你为何会这么认为?”
赵扶桑一愣,看了眼阿辞,继而说着自己的猜测以及感受:“王爷风光恣意,一生骁勇骄傲,因为有她,炙汐域才会迎来太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失踪,在妖都剧变之时还下落不明,一定是出事了,而且,自己的权力才不过短短几日就归于旁人,换做天之骄子,怎能轻易服输。尽管.....尽管.......”
阿辞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问道:“你说就是了。”
赵扶桑看了眼阿辞,接着再次撇开,继而又好像是想到什么,又或是在暗示着什么,说道:“尽管,那个人是她最珍爱之人。”
阿辞却是不解:珍爱?
笑话,珍爱之人会在大婚之日发动政变?珍爱之人会将自己踢进乱葬崖?
若非感受不到情爱,阿辞或许听到赵扶桑说的这些话时早就心底抽疼了。
还会因为这过多的情绪扰乱自己的思绪。
赵扶桑小心翼翼地收回了目光,他知道阿辞一定不懂自己的意思,也不会感受到自己的心意。
瑞羽却点点头:“王爷和王妃之间或许是真爱。听闻这几年里,先王妃还为王爷修建了陵墓,穿着的也是素白衣服,或许是思念王爷。”
阿辞:那他的表面功夫做的还真是不错,搞得他有多么贞烈似的。
赵扶桑这时撇眼看着阿辞:“天若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
阿辞却是负手,神情冷漠,语气冰冷:“天若无道,必会将负心之人万箭穿心。”
寒风幽幽扬起,激的赵扶桑和瑞羽相继后脊一寒。
三人伴着夜色进城。
瑞羽他们安身的地方是城中的一个小镇。
赶过去恐怕还需要两个时辰左右。
他们索性也就在一个驿馆之中休憩下了。
今夜风雪严寒,驿馆内却是热烘烘的,大家坐在饭堂之中吃着饭,门窗将那些风雪隔绝在外,只听得呜呜的呜咽声,小二也是忙的乐在其中,还时不时地与那些客人开着玩笑。
在这样一个热闹的氛围当中,阿辞夹着面前的菜,三人也是相顾不说话。
这时就听到他们旁边的小二笑着上菜,接着就加入了那桌人的谈话中。
“这样的风雪,那些人恐怕不会过来了,三江多么凶险,除了跨越三江,要到达这里,难如登天。”
周围的人哄然一笑。
阿辞则是面不改色着放下了碗筷。
赵扶桑看着他碗中剩的半碗米饭:“是菜不合口味么?”
阿辞摇摇头,倒了杯水,继而将小二给叫了过来。
小二擦着手笑呵呵地:“这位客官,有何吩咐?”
阿辞将一块金子放在桌上,那小二先是一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块金子,紧接着就看到他不动声色地将金子收回自己囊中,他问道:“这位客官,想知道什么?”
阿辞却说:“帮我办件事,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赵扶桑和瑞羽相继一停,也看着小二。
小二面色微顿,接着故作神秘地微微倾身,说道:“客官,什么事?”
阿辞接着将一封信交给小二,说道:“明日清早,将这封信交给军中元川将军。”
小二则是多余的话也不过问,只是将那封信给收下,继而看着阿辞:“客官,说话算话?”
阿辞点点头。
在这里的人,打交道的人那么多,出事总归是圆滑些。
小二走后,又继续无事发生般走走停停,到处上菜。
“你听说赵家的事了么?”一个圆头大耳的人故作神秘地夹着花生问道。
人总是喜欢在吃饭之时谈论一些琐碎的事情。
阿辞则是漫不经心地听着。
另一个人獐头鼠目的人倒着酒,一时间也来了兴致,问道:“哪个赵家?”
圆头大耳的人啧了声,倒也没有不耐烦,反倒带着几分优越感,说道:“这炙汐域内还会有哪个赵家?”
獐头鼠目恍然:“何事何事?”
圆头大耳的人说道:“就在一旬之前,那赵家的小公子南下来做生意,就在花锦城中歇脚,结果你猜怎么着.......”他还故作神秘地一顿。
獐头鼠目也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不会死了吧?”
圆头大耳的人略显夸张地点着头:“对,就死在那月兴楼花魁的花船上。听说,衙门的人到的时候整个人都衣冠不整,甚至........”他轻扫四周,压低声音凑近,再次说道,“甚至四肢都被绑了起来,那命根子都不在了半根。”
说到此时,獐头鼠目更是惊讶:“你咋知道的?”
圆头大耳的人很是得意:“我表兄就在衙门当差,他看见了跟我说的。”
圆头大耳接着说:“我再跟你说,那小赵公子听说找的还不止花魁一人......足足有几十人呐。”
獐头鼠目则是扬起猥琐的笑意:“那他是爽死的吧?还是他会玩。”
可是下一秒,紧接着獐头鼠目的椅子轰然断裂,他重重地摔了个屁股蹲儿,圆头大耳哈哈大笑:“瞧把你激动的,你难不成也想去试试?”
可是下一秒,另一个小二端来了沸腾的汤,脚下不稳,那碗滚烫的汤就这样将那圆头大耳的人从头淋到头。
他痛叫一声,蹦的老高,如同在跳舞般,四处蹦跶着,口中还在骂骂咧咧着。
阿辞撇了眼赵扶桑。
那眼中是深意,是晦暗不明的暗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