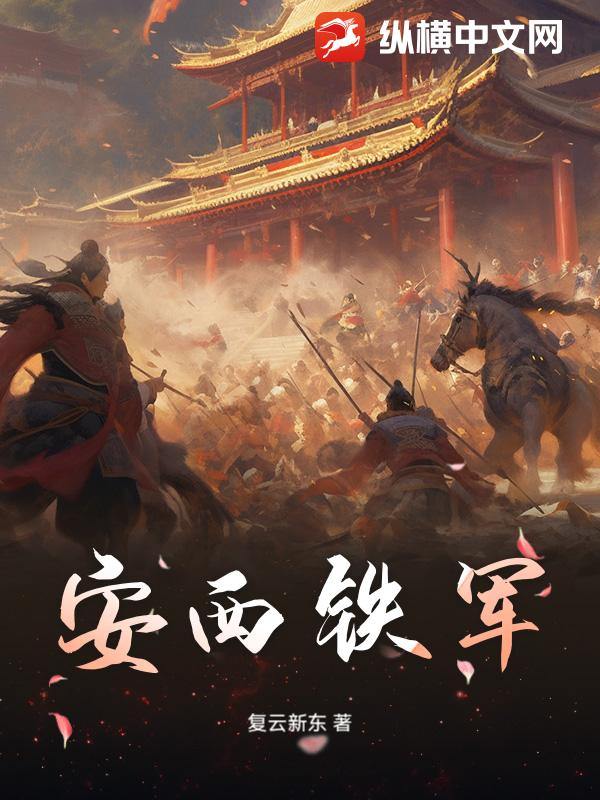豆子左腿的焦骨从皮肉里刺出,像一截被雷火劈断的胡杨枝。溃烂的创口淌着黄绿脓水,腐气混着血腥在军衙里弥漫。孙老拐端来滚烫的醋汤,独臂赵承恩将豆子死死按在门板上。“咬住!”老医官把裹着麻布的柳木棍塞进少年嘴里,烧红的烙铁从炭盆抽出时,火星溅上房梁。豆子眼球暴凸,喉管里挤出野兽般的呜咽,烙铁压上创口的瞬间,焦糊味盖过了所有气息。汗水浸透的门板留下十道带血的抓痕,少年昏死前最后看到的,是郭昕解下猩红披风盖住他残腿的剪影。
王老七缩在角落,枯手反复搓着脸上干结的泥痂——那是昨夜郭昕按在他心口的冻土。他偷眼望向被抬走的豆子,又瞥见北坡焦土里半露的老周门牙,佝偻的背脊剧烈一颤。风雪扑打着窗棂,虎子滚烫的呓语从隔壁传来:“杏花……爹……回家……”妇人压抑的抽泣像钝刀割着每个人的神经。
三更时分,王老七鬼魅般溜到北坡。他用豁口的陶片小心翼翼刨开焦土,将老周的门牙埋进半尺深的冻层。“兄弟……”他对着黑沉大地呢喃,“我替你守着这点念想。”话音未落,脚底突然传来沉闷的震动!
“咚!咚!”
声音来自城墙根!王老七耳廓贴地,脸色骤变——是掘地声!他连滚爬冲向烽燧台,拽响警钟的麻绳却被一刀斩断!三个吐蕃尖兵从雪坑暴起,弯刀直劈他脖颈!
“当!”
断矛架住刀刃!赵承恩独眼在暗夜中凶光毕露:“狗奴敢摸夜路?”他身后,十二名仅存的陌刀手沉默矗立,残刃映着雪光如犬牙参差。王老七趁机扑向军衙嘶吼:“地道!吐蕃狗在挖墙根!”
地听瓮(注:唐代侦测地道用陶瓮)被急速埋入西墙内侧。赵承恩左耳紧贴瓮口,独眼紧闭。豆子的惨嚎、虎子的呓语、风雪的呼号都在耳畔退去,瓮壁传来清晰的刮擦声——来自东南!他猛地睁眼:“离墙十五步!深两丈!三百人正在凿洞!”
郭昕的令旗劈落:“火油灌地道!”
滚烫的油脂顺着竹管倾入探孔。火把掷下的瞬间,烈焰从三处墙基喷涌而出!凄厉的惨嚎穿透土层,焦肉味混着泥土的腥气弥漫全城。侥幸钻出的吐蕃兵被陌刀剁成肉泥,王老七疯抢了一柄弯刀,砍卷刃了也不停手,污血泼满他枯树般的脸。
达扎路恭的金盔在黎明时染上寒霜。他冷眼看着焦尸被拖出地道,马鞭突然指向龟兹城头:“压上去。”
这一次,没有草甲,没有云梯。三队赤膊的奴隶被驱赶到阵前,每人背着一筐冻土。“填!”通译的嘶喊劈开寒风,“用汉奴的骨头垫路!”鞭影翻飞中,奴隶们哀嚎着将冻土抛入冰壕,吐蕃重甲步兵紧随其后,巨盾组成移动的铁壁,向着昨夜焚毁的东墙缺口缓缓推进。
十二柄陌刀在缺口后列成楔形。刀柄缠着浸血的布条,白发老卒们用豁口的刃面互相打磨,金属刮擦声压过了吐蕃的皮鼓。“陌刀阵,三才锋矢。”郭昕的声音平静无波,“今日之后,世间再无安西陌刀。”
王老七突然挤到阵前,将一颗带血的牙拍进郭昕掌心——是昨夜他从焦尸嘴里掰下的吐蕃兵门牙。“给豆子……凑一对。”他咧嘴,露出仅剩的三颗黄牙。郭昕攥紧那颗沾血的敌齿,冰凉的触感直透骨髓。
重甲步兵的巨盾撞上断墙的刹那,十二道雪瀑般的刀光轰然倾泻!碎盾与断肢齐飞,第一排便被绞成肉酱!但第二排、第三排的弯刀从尸堆后刺出,陌刀手接连倒下。赵承恩独臂斩断一柄刺向王老七的矛头,自己肋下却被弯刀捅穿!
“老赵!”王老七目眦欲裂。
“走!”赵承恩用身体压住敌刀,独臂将王老七踹向后方,“护住……苗!”
最后三名陌刀手背靠背挺立,残刃滴血。吐蕃兵如狼群环伺,却无人敢近。达扎路恭的金盔在坡顶微动,一队弓箭手越众而出。
“举旗……”郭昕的鸣镝射向苍穹。残破的唐字旗在尸山血海上艰难升起,裹着硝烟猎猎狂舞。箭雨遮蔽天光的刹那,三柄陌刀最后一次挥出半弧——像极了北坡那三株被风雪压弯又倔强挺起的麦苗。
王老七背着昏迷的豆子冲上北坡时,虎子正用小手抠开焦土。那颗黄浊的老周门牙在晨光中露出全貌,下面竟压着一星惨绿的嫩芽!焦黑的麦秆根部,新芽如匕首刺破死亡。
“活了……”王老七的泪砸在嫩芽上,“兄弟……苗活了……”
城头的唐字旗轰然倒下,溅起一片血红的雪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