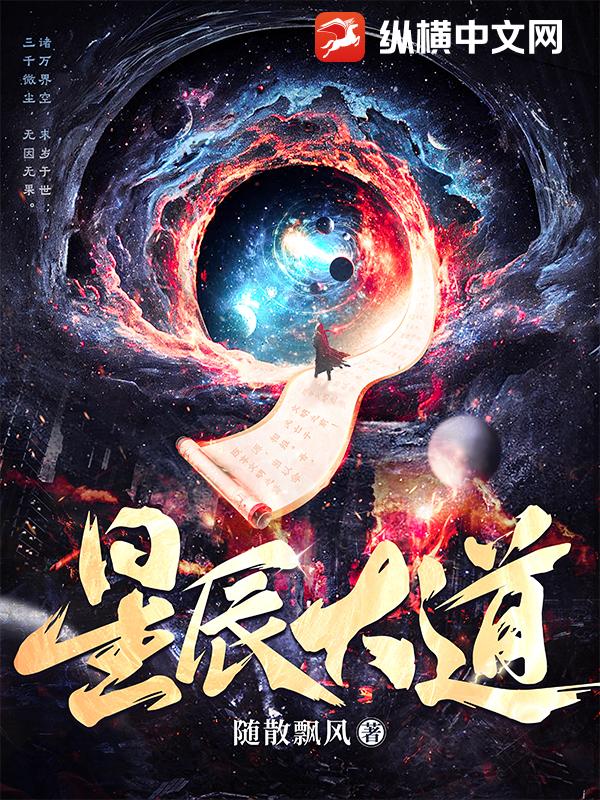队长攥着那枚粉色发卡往回走时,雨势终于弱了些,从先前的“灌”变成了“浇”,砸在雨衣上的声音也轻了,不再是“砰砰”的闷响,而是细密的“沙沙”声,像有人在耳边翻着旧报纸。
巷口的警戒线还拉着,几个年轻警员正围着技术员说话,手电筒的光柱在雨里晃来晃去,偶尔照到墙根的积水,能看见里面浮着的碎纸和落叶。他刚钻过警戒线,派出所的小年轻就凑了过来,手里攥着个湿透的笔记本,笔尖还在滴水:“队,法医刚打电话,说路上的树倒了,还得二十分钟才能到。刚才我们又在巷子里扫了一遍,除了您捡的那个发卡,啥也没找着——连个完整的鞋印都没有,雨水全给冲平了。”
队长“嗯”了一声,把发卡塞进雨衣内侧的口袋里——那里贴着胸口,能感受到塑料壳子的凉意透过布料传过来,像块小冰碴。他抬头看了眼永安巷的深处,青石板路在雨雾里延伸,两边的老房子门扉紧闭,只有巷尾那家的空调外机还在嗡嗡转,声音比刚才弱了些,像是快没力气了。“通知技术队,把巷口那台旧监控的硬盘拆了,不管能不能用,先带回去恢复数据。另外,挨家挨户敲门问问,就算是老人,也可能听见或看见点什么——重点问有没有人见过穿浅灰色外套的小孩。”
“好嘞!”小年轻应得快,转身就往巷口跑,雨靴踩在积水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腿,他也没顾上擦。
队长又蹲回死者旁边,蓝布被雨水泡得更沉了,掀开时能听见布料摩擦的“窸窣”声。死者的脸还是那样,眼睛睁着,瞳孔散得很大,眼白上的血丝像蛛网似的。他又看了眼死者攥紧的左手,指缝里的浅黄纸角被雨水泡得更软了,隐约能看见“便利店”三个字的轮廓,却还是看不清具体信息。他伸手碰了碰死者的手腕,皮肤已经凉透了,僵硬得像块硬纸板——死亡时间应该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刚好是暴雨最猛的时候。
“队,您手机响了。”旁边的技术员突然提醒道。
队长这才想起掉在副驾驶座下的手机,刚才追小孩时忘了捡。他站起身,拍了拍雨衣上的水,“我回去拿趟手机,顺便跟局里汇报下情况,你们在这儿守着,别让无关人员进来。”
往巷子口走时,他又看了眼巷尾的拐角——那里空荡荡的,只有绿色垃圾桶歪在墙边,盖子被风吹得“哐当”响,里面的污水顺着桶缝往下滴,在地面积了个黑褐色的小水洼。他摸了摸胸口的口袋,发卡还在,硬硬的,硌得他心口有点发慌。
车子里的凉气还没散,坐进去时能感觉到后背的雨衣在往下滴水,很快就把座椅洇湿了。他弯腰在副驾驶座下摸了半天,才摸到手机——屏幕贴着点泥,边缘还沾着根头发,是妻子的长头发,上次她坐副驾驶时掉的。解锁屏幕,第一条就是妻子半小时前发的消息:“女儿又醒了,哭着要找爸爸,我给她冲了杯热牛奶,现在哄睡着了,你注意安全,别淋着雨。”
下面还有条两分钟前的未读消息:“刚听见窗外有脚步声,好像在门口停了会儿,不过应该是错觉,你别担心。”
队长的手指顿在屏幕上,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眼后视镜,雨幕里只有永安巷口的警灯在闪,红蓝色的光映在车窗上,晃得人眼睛发花。他赶紧给妻子回了条消息:“我这边忙完就回去,你把门锁好,别给任何人开门。”
发完消息,他又给局里的值班领导打了个电话,简单汇报了现场情况——无名男尸,锐器致死,现场遭暴雨破坏,目击者称有一名穿浅灰色外套的儿童出现,目前未找到更多线索。领导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老陈,你多费心,最近市里要创文明城,这种命案不能拖。另外,注意安全,听说永安巷那片不太平,之前有居民反映过晚上有陌生人晃悠。”
“知道了。”挂了电话,队长捏了捏眉心,感觉太阳穴有点发紧。他发动车子,雨刮器还在左右扫着,这次终于能看清前面的路了——路面的积水反射着路灯的光,像铺了层碎玻璃。
往家开的路上,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像有块石头压着。妻子刚才说“听见门口有脚步声”,他家住在三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快一个月,每次晚上回家,都得跺脚才能让灯亮。如果真有人在门口徘徊,妻子肯定能听见脚步声——那脚步声会在三楼停住,然后是钥匙碰锁的声音,或者是……敲门声?
他越想越慌,脚下不自觉地踩重了油门,车子的引擎发出“嗡嗡”的闷响,像头喘着气的老牛。路过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时,他看见里面亮着灯,柜台后坐着个打哈欠的店员,玻璃门上贴着“24小时营业”的贴纸,被雨水泡得有点卷边。他突然想起死者指缝里的便利店收据——会不会就是这家?
但他没停车。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家看看妻子和女儿,那枚发卡像根刺似的扎在他心里,让他坐立难安。女儿的发卡是上周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的,粉色的,水钻掉了一颗,当时女儿还哭了半天,说“不好看了”,是他哄着说“这样更特别”,女儿才肯戴的。永安巷离他家小区有三公里远,怎么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发卡?
车子刚拐进小区,他就看见自家单元楼的灯亮着——三楼,客厅的灯,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缝照出来,在地面的积水上映了个小小的光斑。他松了口气,应该是妻子还没睡,在等他。
停好车,他抓起雨衣往楼上跑。楼道里果然一片黑,他跺了跺脚,声控灯没亮,只能摸着墙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楼梯板“吱呀”响,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楚。走到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平台时,他突然听见上面传来“咚”的一声,像是有人碰了门。
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枪没带在身上,早上换衣服时忘在抽屉里了。他只能放慢脚步,一步一步往上挪,耳朵贴在墙上听着上面的动静。
没有声音。只有雨水顺着楼道窗户往下滴的“滴答”声,还有自己的呼吸声,很重,像台破旧的风箱。
走到三楼门口时,他看见门是虚掩着的,留了条缝,里面的橘黄色灯光从缝里漏出来,在地面映了道细长的光。他的心脏“砰砰”跳得更快了,手放在门把手上,指尖有点发颤。
“咔哒”一声,他轻轻推开了门。
客厅里没人,电视关着,茶几上放着个空牛奶杯,杯沿还沾着点奶渍,旁边是女儿的小熊玩偶,歪在沙发上,身上盖着条小毯子。阳台的窗户开着条缝,风裹着雨丝吹进来,把窗帘吹得“哗啦”响。
“老婆?”他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没人应。
他赶紧往卧室走,卧室的门也是虚掩着的,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轻轻推开门,看见妻子和女儿躺在床上,盖着同一条被子。妻子的头发散在枕头上,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什么梦;女儿蜷缩在妻子怀里,小脸蛋红红的,嘴角还带着点笑,手里攥着个小恐龙玩具——那是他去年出差时给女儿买的。
队长站在门口,看着床上的母女俩,紧绷的弦瞬间松了下来,后背的冷汗顺着脊椎往下流,把里面的衬衫都浸湿了。他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女儿的额头,温温的,没发烧。又摸了摸妻子的手,也是暖的。
他松了口气,转身想把阳台的窗户关上——风太大了,别让母女俩着凉。走到阳台时,他看见窗台上放着个东西,是女儿的粉色发卡,水钻掉了一颗,安安稳稳地躺在窗台上,旁边还放着女儿的小发绳。
他的心又猛地一紧。
女儿的发卡明明在窗台上,那永安巷巷尾捡到的发卡,是谁的?
他拿起窗台上的发卡,和胸口口袋里的发卡对比了一下——一模一样,都是粉色的塑料壳子,水钻都掉了一颗,连掉的位置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窗台上的发卡很干净,没有泥;而口袋里的发卡,还沾着点青石板路的青苔碎屑。
他靠在阳台的墙上,看着外面的雨——雨已经很小了,变成了毛毛雨,落在楼下的香樟树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远处的路灯亮着,光透过雨雾,变得柔和了许多。他摸了摸胸口的口袋,那枚沾着泥的发卡还在,硬硬的,硌得他心口发疼。
这时候,卧室里传来女儿的呓语:“爸爸……发卡……”
队长赶紧把口袋里的发卡拿出来,塞进裤子口袋里,又把窗台上的发卡放回原位,轻轻掖了掖女儿的被子。女儿翻了个身,继续睡了,小嘴巴还在动,像是在说什么悄悄话。
妻子也醒了,揉了揉眼睛,看见他站在床边,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回来了?这么晚,还以为你要在局里过夜呢。”
“现场处理得差不多了,回来看看你们。”他坐在床边,伸手把妻子额前的头发捋到耳后,“刚才你说听见门口有脚步声?”
“嗯,大概半小时前吧,”妻子打了个哈欠,“我听见脚步声从楼下上来,在门口停了会儿,还以为是你回来了,结果等了半天也没敲门,我就又睡着了。可能是隔壁张阿姨家的儿子回来了吧,他最近总加班。”
队长没说话,心里却犯了嘀咕。隔壁张阿姨的儿子住四楼,脚步声应该往四楼去,怎么会在三楼门口停住?而且他刚才上来时,楼道里根本没人。
“对了,女儿的发卡找到了,”妻子指了指窗台,“早上她还哭着说找不到了,结果刚才我收拾阳台时,在窗台上看见了,可能是昨天晒衣服时掉的。”
“哦,是吗?”他勉强笑了笑,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可能吧。”
妻子没察觉到他的异常,打了个哈欠又躺下了:“你也早点睡吧,看你累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嗯,我去洗个澡就睡。”他站起身,轻轻带上门,走到客厅。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响,指针指向凌晨四点半。他坐在沙发上,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枚沾着泥的发卡,放在茶几上。发卡上的泥已经干了点,变成了灰褐色,粘在粉色的塑料壳上,显得格外刺眼。
他拿起手机,给技术队的小李发了条消息:“帮我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儿童失踪案,尤其是戴粉色发卡、水钻掉了一颗的小女孩。另外,查一下永安巷附近的小卖部,有没有卖过这种发卡。”
小李很快回复:“好的陈队,我现在就查,有结果了马上告诉你。”
放下手机,他盯着茶几上的发卡,脑子里乱得像团麻。永安巷的死者,穿浅灰色外套的小孩,一模一样的发卡,门口的脚步声……这些碎片像散落在地上的珠子,他找不到线,串不起来。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早上出门时,女儿说过一句话:“爸爸,昨天晚上我看见窗外有个小哥哥,穿灰色的衣服,站在楼下看我们家。”当时他以为女儿是在说梦话,没当回事,现在想来,女儿说的“小哥哥”,会不会就是派出所小年轻看见的那个穿浅灰色外套的小孩?
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如果女儿说的是真的,那这个小孩为什么要盯着他家看?为什么会出现在永安巷的案发现场?那枚沾着泥的发卡,又是怎么回事?
他站起身,走到阳台,往下看。楼下的花坛里积了水,映着楼上的灯光,像个小小的镜子。花坛旁边的小路空荡荡的,只有风吹着香樟树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没有小孩,也没有脚步声。
但他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他,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家里的一切。
他摸了摸腰间,想起枪还在抽屉里,赶紧走到书房,打开抽屉,把枪拿出来,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又走到门口,检查了门锁——是反锁着的,没问题。
回到客厅,他又拿起那枚沾着泥的发卡,放进一个密封袋里,然后塞进抽屉的最里面,和枪放在一起。他不想让妻子和女儿看见这枚发卡,不想让她们担心。
雨已经停了,天边泛起了一点鱼肚白,透过阳台的窗户照进来,在客厅的地板上映了道细长的光。墙上的挂钟“滴答”响着,新的一天开始了,但对队长来说,这一夜的谜团,才刚刚开始。
他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死者睁着的眼睛,想起了女儿的呓语,想起了门口的脚步声。那枚粉色的发卡,像个幽灵似的,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提醒着他,这场暴雨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命案,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危险,正悄悄围绕着他的家。
烟燃尽了,烫到了他的手指。他猛地回神,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站起身,走到卧室门口,轻轻推开一条缝——妻子和女儿还在睡,呼吸均匀,脸上带着平静的笑意。
他心里暗暗发誓,不管那个穿浅灰色外套的小孩是谁,不管这枚发卡背后藏着什么秘密,他都要查清楚,一定要保护好妻子和女儿,不能让她们受到任何伤害。
窗外的天越来越亮,阳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把卧室里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但队长知道,有些阴影,不会随着阳光的到来而消失,它们会藏在角落里,等着下一个雨夜,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