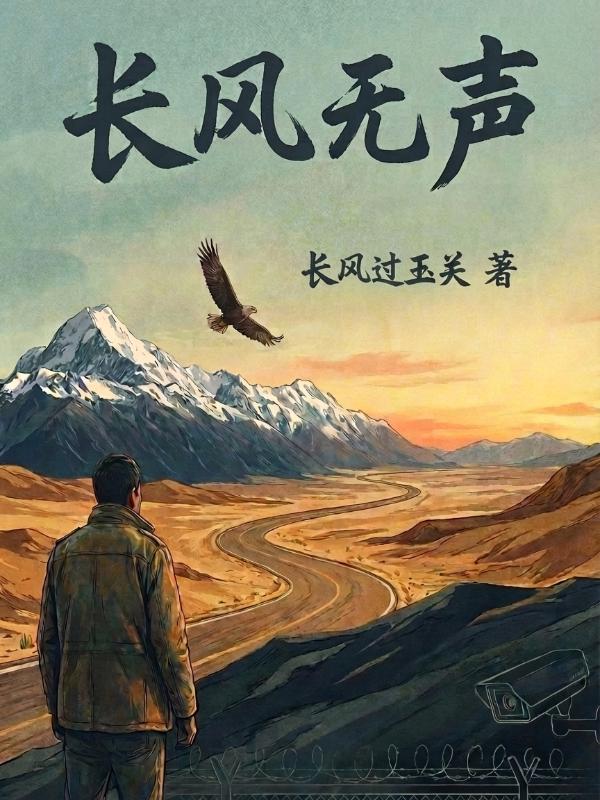(1)
凌晨六点半,乌鲁木齐的天还是黑的。
艾尔肯·托合提从租住的老小区单元楼出来,把冲锋衣拉链往上拽了拽,三月的风很硬,像天山那边刮过来的刀片,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没有阻挡,他早习惯了这样的冷,就像习惯独居、失眠,还有前妻热依拉时不时在微信上发来的关于女儿娜扎的生活视频一样,他不会去要,但是每条都会看很多遍,把那几十秒的画面印在脑海里。
车停在路边,挡风玻璃上结着一层霜,他没开暖风,直接点火。
去母亲的馕店,这每周至少两次是必须的,不是帮什么忙,他母亲帕提古丽从不需要别人帮忙,确切地说是他需要那个地方,需要馕坑里跳跃的火苗,需要面团摔打在案板上的声音,需要挂在收银台后面的那张父亲的遗照。
二十分钟之后,他把车停在二道桥那边的小巷子口。
老城区慢慢睁开眼,几家早点铺子亮着灯,蒸笼的白气从门缝里钻出来,碰到冷空气就变成一阵若有若无的雾,艾尔肯路过的时候,卖羊杂碎的老汉朝他点个头:“艾尔肯,来一碗?”
“等下马大叔,先去我妈妈那边。”
“你妈六点就起了。”老汉感叹,“帕提古丽的馕,这条街谁不认?就是太辛苦。”
艾尔肯没接话,快步往前走。
馕店的招牌依旧是那块木板,上面刻着维汉两种文字“托合提馕饼”,在招牌之下,父亲的照片被装进玻璃框中,全天都有一个小灯照亮,照片中的托合提·艾山身着警服,胸前挂着立功勋章,神情平和,嘴边似乎有笑——或许是照片模糊的缘故。
艾尔肯推门进来。
热气扑到脸上,有麦香味,还有芝麻香,还有馕坑的特有香味,帕提古丽正在弯腰往馕坑里贴面饼子,她的动作很熟练,像台机器一样精准,她今年六十大寿,头发全白了,但身体还是很利索。
“妈。”
帕提古丽头也不抬:“灶台边有茶壶,自己倒。”
艾尔肯走到灶台旁边,拎起保温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奶茶,维吾尔族的奶茶是咸的,放一点点胡椒和酥油,他小时候不爱喝这个,觉得味道怪,现在倒是戒不掉,特别是从母亲这儿喝到的。
“案板上的面切了。”帕提古丽终于直起腰来,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回头看了儿子一眼,“黑眼圈又重了,你是不是又一整宿没睡?”
“睡了。”艾尔肯端着茶杯走向案板,“就是醒得早。”
帕提古丽没说话。
她晓得儿子的工作性质,或者说,她大概晓得,艾尔肯从不跟她说工作的事,她也不问,这是托合提·艾山在世的时候定下的规矩,国安干警的家属,第一课就是学会沉默,帕提古丽学得很不错,她把所有的担心都揉进面团里,摔在案板上,贴进馕坑里,再用火烤成金黄酥脆的饼。
艾尔肯拿起面刀,把一大块发好的面团分成等分,动作生疏,帕提古丽看不过眼,走过来把他挤到一边。
“你那手是拿枪的,不是做馕的,让开。”
“我如今不拿枪。”艾尔肯往后退了一步,靠着墙,望着馕坑里跳跃的火苗,“我现在主要是对着电脑。”
“电脑。”帕提古丽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字眼,声音里有些复杂,“你爸要活着,肯定不会学电脑,他这辈子只会两样东西,骑马和开枪。”
“爸那会儿不需要电脑。”艾尔肯说,“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不一样了,坏人还是坏人。”帕提古丽把分好的面团排列整齐,开始一个一个地揉圆、擀平、用馕戳子在中间戳出花纹,“你爸说过,不管用什么手段,坏人想害咱们这片土地的心不会变。电脑也好,刀子也好,都是工具。人心才是最要紧的。”
艾尔肯没有接话。
他想起父亲最后一次跟他说话的情景。托合提·艾山打电话来,背景音很嘈杂,似乎是在街上。
“儿子,你回来吧。”父亲说,“这边需要你。”
“爸,我还没想好……”
“想什么?”父亲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肃,“你学的那些东西,用在赚钱上,可惜了。回来,守护这片土地,不只是拿枪的事。以后的仗,要在你们年轻人懂的那些地方打。”
三天后,托合提·艾山在处置一起暴恐事件时殉职。遗体运回来的时候,艾尔肯还在从北京赶回乌鲁木齐的火车上。
那是他这辈子最长的一次火车旅程。窗外的戈壁滩一成不变地往后退,他盯着那些荒芜的土地,脑子里反复回放父亲最后那句话:回来,守护这片土地,不只是拿枪的事。
后来他进了国安系统。父亲说得对,以后的仗,确实要在年轻人懂的那些地方打。
馕坑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把帕提古丽的影子映在墙上,艾尔肯看着那个影子,忽然觉得母亲老了,她弯腰的幅度比去年还大,直起身子时总会扶一下腰,可是她从不叫苦叫累,也不抱怨,托合提·艾山离开后,她就这样一个人扛着这家馕店,整整十五年。
“妈,雇个人吧。”艾尔肯说,“我给你钱。”
“雇人?”帕提古丽嗤笑一声,“我这馕是手艺活,雇来的人都烧不出那个味儿,再说我要是空下来天天在家里想着你爸,我不得疯掉。”
这话让艾尔肯心里很不舒服。
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就在这时候震动了起来。
他掏出来瞅了眼——林远山。
四处处长,他的直接领导,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准没什么好事。
“妈,我接个电话。”
帕提古丽挥挥手,继续往馕坑里贴饼子。
艾尔肯走出店铺,站在招牌底下接电话,早晨的冷风吹进领口,他一下子清醒过来。
“处长。”
“在哪?”林远山的声音还是跟以前一样沙哑,好像一夜没睡,“你妈那里?”
“嗯。”
“能脱开身吗?局里有事。”
“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林远山很少会这样沉默,他一沉默就说明事情很麻烦。
“阿勒泰那边,某县。”林远山声音更低了,“网上突然出现很多舆情,就像群事件的火苗一样,但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数据有问题,你来看看。”
“多大规模?”
“目前还不好说,帖子在境内的几个平台上同时冒出来,时间上高度一致,话术也高度雷同,古丽娜昨晚加班跑了个初步分析,她说这批内容的生成模式不太像是自发的。”
艾尔肯皱起眉头。
群体事件本身不归国安管,那是维稳部门的职责。如果舆情的生成模式“不像是自发的”,那就意味着背后存在组织化的操控,而组织化的舆情操控,多半与境外势力有关。
“我半小时就到。”
“行。”林远山顿了顿,“早饭带着路上吃,今天估计有得熬。”
电话被挂断。
艾尔肯在冷风中站了几秒,转身推开了馕店的门,帕提古丽正在从馕坑里取出一批烤好的馕,金黄色,香喷喷的。
“妈,我得走,单位有事。”
帕提古丽没抬头:“又是临时的?”
“嗯。”
“等等。”她放下馕戳子,从案板边的筐里拿出两个刚出炉的馕,用牛皮纸袋装起来,递给艾尔肯,“带着路上吃,别饿着肚子干活。”
艾尔肯接过纸袋,馕的热度透过牛皮纸传到掌心,他低头瞧了瞧,馕饼表面撒着芝麻和洋葱碎,是父亲生前最爱吃的那种。
“妈,我走。”
“去吧。”帕提古丽转身继续干活,背对着他说道,“注意安全。”
这四个字,她说了十几年,每次艾尔肯要走,她都会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叮嘱儿子带钥匙,但是艾尔肯知道,这四个字有多重,托合提·艾山出门执行任务的时候,她也是这样说的。
那次,她丈夫就没再回来。
艾尔肯推开房门,凌晨的冷风扑面而来。
他回过头看了眼馕店的招牌,父亲的照片在小灯下格外清晰,就像在目送着他一样,艾尔肯就站在那里望着照片,突然间想起了父亲生前跟自己说过的一句维吾尔族谚语:
“沙漠里的火,看起来很小,但是可以给夜里赶路的人带来光亮。”
他把馕塞进冲锋衣口袋里,转身就朝巷口那辆车走去。
(2)
新疆安全厅四处的办公区,就藏在市区的一栋不起眼的建筑里,门口没有任何标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写字楼,这是有规定的,隐蔽战线的单位不能太张扬,艾尔肯每次进出这栋楼,都觉得像是在公司上班的白领一样——除了进门要过三道安检,除了楼里没有一扇朝外开的窗户。
林远山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
他五十岁,身体很强壮,脸上有几道很深的伤疤,那是以前在南疆参加反恐行动留下的,他穿一件起球的羊毛衫,手里拎着个水杯,里面泡着颜色发黑的枸杞茶。
“来了?”他看见艾尔肯进来,下巴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上一扬,“自己看。”
艾尔肯坐下来,把笔记本拉到跟前。
眼就看见了是技术科的古丽娜连夜赶制出来的舆情监测报告,艾尔肯只是粗略地扫了一下重点。
时间节点——阿勒泰某县负面帖子爆发时间为昨晚11点至凌晨2点
内容主题——该县某征地项目“强拆”谣言、少数民族干部“欺压百姓”的不实指控、一段“现场画面”的病毒式流传。
传播特征——一小时左右大量账号发类似帖子,帖子使用相同的表情包及配图,部分账号注册时间在近三个月内且此前无历史发帖。
古丽娜在报告末尾加了一条备注,初步判定这批东西是有组织投放的,要追踪境外关联。
艾尔肯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开始在桌面上敲打。
“视频看了吗?”他问林远山。
“看了。”林远山把水杯放回桌上,“剪辑痕迹很重,画面里的人说的话跟字幕对不上,古丽娜说那段音频可能是后期合成的,用的是某种语音生成软件。”
“发帖账号的IP呢?”
“大部分显示在境内,十几个省市,”林远山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但你明白这说明不了什么。”
艾尔肯点点头。
境外势力做舆情渗透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借助跳板和代理,从表面上看,这些帖子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普通网民发出来的,但背后真正的操控者也许相隔很远,甚至就在国境之外。
“我要原始数据。”艾尔肯说:“让古丽娜把那个发帖的账号信息、注册时间、活跃时段、互动模式都列出来,越详细越好,还有那视频的元数据,如果能得到的话。”
“数据已经准备好了。”林远山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艾尔肯说道,“我叫你来不仅仅是为了分析数据。”
艾尔肯抬起头:“还有什么?”
林远山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阿勒泰那边的县,有个你老熟人最近突然回来了。”
“谁?”
“阿里木·热合曼。”
艾尔肯的手指停止了敲击。
阿里木。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撬开了他记忆深处某扇紧闭的门。
“他回来了?”艾尔肯的声音有点发紧,“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林远山盯着他的脸,“你们是发小,对吧?我知道。”
艾尔肯没说话。
他确实和阿里木是发小。两家住得近,父母关系好,小时候一起上学一起踢球一起在巴扎上偷吃羊肉串。阿里木的父母早亡,托合提·艾山曾经资助他念完高中、念完大学,直到他出国留学。那之后,两人就渐渐断了联系。艾尔肯进了国安系统,阿里木据说在国外创业,开了一家IT公司。
“他回来干什么?”艾尔肯问。
“不清楚。”林远山摇摇头,“但他回来的时间点太巧了。上个月从边境到阿勒泰,这个月那边就出事。你不觉得蹊跷?”
艾尔肯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他当然觉得蹊跷。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情报工作没有巧合这回事。时间节点的吻合,往往意味着因果关系的存在。
但他同时也知道,怀疑一个人是需要证据的。尤其是怀疑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不,应该说是曾经的朋友。他们已经十年没联系了。十年,足够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先查舆情的源头。”艾尔肯睁开眼睛,声音恢复了平静,“阿里木的事,如果有关联,数据会告诉我们。”
林远山看了他几秒,点点头:“行。你自己把握。”
(3)
技术科的办公室在三楼,整层都是服务器的嗡嗡声和空调的冷风。
古丽娜·阿不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前摆着三台显示器,手边是喝了一半的美式咖啡。她二十八岁,短发,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印有漫画图案的卫衣,看上去更像个大学生而不是国安干警。
“艾处,您来得正好。”她看见艾尔肯走过来,转动椅子面向他,“我刚跑完第二轮分析,有发现。”
“什么发现?”
古丽娜把其中一台显示器转向艾尔肯,上面是一张复杂的网络拓扑图,节点之间用不同颜色的线段连接着。
“这是那批发帖账号的关联图谱。”她用激光笔指着其中几个节点,“看这几个,它们是最早发帖的种子账号。时间精确到秒,比其他账号早七分钟。”
“七分钟够干什么?”
“够那段视频在小范围内预热发酵,然后由后续账号集中转发扩散。”古丽娜推了推眼镜,“这是标准的舆情投放模型,国内一些营销公司也会用。但有意思的是,我追查这几个种子账号的注册IP,发现它们不在境内。”
艾尔肯眯起眼睛:“在哪儿?”
“表面上是土耳其,但我进一步穿透代理层之后,发现底层流量有一部分经过了M国弗吉尼亚州的某个服务器集群。”古丽娜把另一份文档调出来,“弗吉尼亚,您懂的。”
艾尔肯当然懂。
弗吉尼亚州兰利,这是M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所在地,一个服务器的具体位置不能说明什么,不过在情报分析界,地理坐标常常带有一种隐喻意味,或者说是一种挑衅。
“继续查。”艾尔肯说,“特别是那段视频,看能不能找到最初的上传者。”
“已经在跑了。”古丽娜点了点头,“但是艾处,还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确定要不要说……”
“说。”
古丽娜迟疑了一下,把第三台显示器转过来,上面是一份商业注册信息查询的结果。
我顺手查了下阿勒泰那个县近半年企业注册的情况,发现有个名字叫“北疆数云”的科技公司,上个月刚落户,”她停顿了一下,“法人代表叫阿里木·热合曼。”
艾尔肯盯着屏幕上那个名字,一言不发。
“我不知道这人和舆情事件有没有关系。”古丽娜小心翼翼地说,“但一家科技公司在那个时间点落户,然后那边就出现了有组织的网络舆情……我觉得需要关注。”
“关注是应该的。”艾尔肯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把这家公司的所有公开资料都调出来,股权结构、合作伙伴、业务范围,一个不漏。”
“明白。”
艾尔肯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古丽娜,这件事暂时不要和别人讨论。”他没有回头,“包括林处那边,我来汇报。”
“收到。”
(4)
中午,艾尔肯没去食堂,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啃母亲给的馕。
馕已经凉了,但嚼起来依然有麦子的甜香。他吃得很慢,目光落在桌上的一张照片上——那是他和阿里木的合影,摄于二十年前,两人都还是穿着校服的少年。照片里的阿里木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牙,胳膊搭在艾尔肯肩上,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梦。
这张照片本来不该出现在他办公桌上。
今天早上,他特意从家里翻出来的。
艾尔肯知道自己不应该感情用事。情报工作的第一条铁律就是客观——所有的判断都必须基于证据,而不是记忆、情感或主观推测。但他也是人。他无法假装自己和阿里木之间没有过那些年少时光。他无法否认,当林远山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心跳确实加速了。
阿里木出国留学那年,正好是托合提·艾山殉职后的第二年。
他记得阿里木临走前来找过他,在托合提·艾山的墓前站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艾尔肯,托合提叔叔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好的人。我会记住他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十年的杳无音信。
艾尔肯曾经试图联系过阿里木,但对方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微信不回,邮件不回,电话打不通。他曾经托人去阿里木读书的那所M国大学问过,得到的答案是:毕业后去向不明。
一个人怎么会去向不明?
除非他不想被找到。
艾尔肯放下手里的馕,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阿里木,眼睛清亮,没有一丝杂质,二十年前的阿里木,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会被坏人利用,变成破坏自己家乡安宁的工具吗?
艾尔肯不愿相信。
他明白,不愿意相信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他的手机就在这时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阿勒泰。
艾尔肯盯着屏幕看了三秒,按下了接听键。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个他很久没听过的熟悉的声音——有点哑,也有点累,但是还是能认出来。
“艾尔肯,是我,阿里木。”
艾尔肯攥紧手机,指节泛白。
“……十年了。”他说,“你终于想起我了。”
“我一直没有忘记你。”阿里木的声音在电话里飘来荡去,好像信号不太好,“我只是……有些事情不方便联系,你应该能理解。”
“我了解什么?”
“我听说你在政府工作。”阿里木笑了,笑得有些苦涩,“托合提叔叔肯定很高兴,他儿子接了他班,守着咱们的家。”
艾尔肯没接话。
他的脑子如同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各种各样的想法在脑海中翻滚,阿里木这时候打电话过来,是巧合还是有鬼?如果阿里木真的牵扯进去,这个电话是试探还是求救?
“阿里木。”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你怎么回来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下来。
“做生意。”阿里木的声音有些干涩,“我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就想回来看看,阿勒泰这边有政策扶持,我就注册了个公司,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在怀疑我?”阿里木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尖锐,“艾尔肯,我们是发小,从小一块儿长大,你爸供我上学,要是没有他,我大概早就死在街头了,你觉得我会做出对不起你们家的事情吗?”
艾尔肯闭上眼睛。
记忆像潮水一般涌来——两个少年夏天在河边打水仗,冬天在雪地里打雪仗,坐在托合提叔叔的摩托车后座上迎着风唱歌……那些日子仿佛已经过去很久远了,但又好像就在眼前。
“我没怀疑你。”他说道,声音压得很低,“但是我得知道,阿勒泰那边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消息。”
“什么事?”
“网上那些帖子和视频,你应该看到了吧。”
阿里木沉默了很久,久到艾尔肯以为电话断了。
“我看到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变得异常疲惫,“艾尔肯,有些事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说一句——那些东西不是我做的,我也不想牵扯进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见你一面。当面谈。”
“当面谈什么?”
“谈……我这十年都经历了什么。”阿里木的声音突然颤抖了一下,“艾尔肯,我可能惹上麻烦了。很大的麻烦。我需要你的帮助。”
电话挂断了。
艾尔肯握着手机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进来,在他身上投下一条条明暗交错的光影。他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守护这片土地,不只是拿枪的事。
也许,这一次的仗,比拿枪更难打。
(5)
与此同时,一千公里之外。
中亚某国首都的一栋公寓楼里,一场视频会议正在进行。
房间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唯一的光源来自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被分成几个窗格,每个窗格里都是一张人脸——或者说,一张被阴影遮挡、只能看见轮廓的人脸。
杰森·沃特斯坐在镜头前,手边放着一杯威士忌。
他四十八岁,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灰色羊绒衫,看上去更像个大学教授而不是情报官员。事实上,他确实在中国某所大学做过两年访问学者,用“文化交流”的名义接触过那个国家的年轻人——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第一阶段投放效果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他开口说话,英语里掺杂着一点德州口音,“舆论发酵的速度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目标地区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下一步我们需要在线下配合做些事情。”
屏幕右上方窗格里,那人磕磕绊绊地说着英语,“我们准备好了,‘雪豹’和他的手下已经在边境等着了,就等您一句话。”
“别急。”杰森举起威士忌酒杯,慢慢摇晃,深红色的液体沿着杯壁缓缓滑落,“中国人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欲速则不达’,我们的计划是长期的,第一阶段只是摸一摸他们的底,看他们有多快的反应速度,真正的动作是在第二阶段才开始的。”
“那个科技公司怎么样?”另一个窗格里的人问,“您安排的那个棋子可靠吗?”
杰森微微一笑。
“阿里木?他是个聪明人,但聪明人往往有聪明人的弱点——他们太在乎自己,也太在乎曾经失去的东西。”他放下酒杯,“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把他培养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以为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创业者,借助我们的资金和资源在中国做生意。他不知道,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他也不知道,他那家公司的服务器,从第一天起就被我们植入了后门。”
“如果他反水呢?”
“他不会。”杰森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一个人一旦踏上了某条路,就很难回头了。更何况,我们手里有他的把柄。他在M国留学时做过的那些事,如果被公开,足够让他在中国坐上十年牢。他除了听我们的话,还有别的选择吗?”
视频会议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讨论结束后,杰森关闭电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外面是中亚城市的夜景,灯火稀疏,和他记忆中的北京、上海完全不同。那些中国的大城市有着令人眩晕的繁华,霓虹灯把夜空都染成粉红色,年轻人在街头笑着聊天,对未来充满信心。
杰森喜欢中国。
他喜欢那里的文化、美食、甚至那些他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诗词。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有时候心烦的时候就翻开来读几首。他最喜欢的一首是王维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那是多么壮丽的意象。
但壮丽归壮丽,工作归工作。他的职责是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而中国,恰好是那个必须被遏制的对手。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只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这片土地的稳定,对他背后的雇主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必须想办法让它不那么稳定。
这就是游戏规则。
杰森端起威士忌杯,对着夜空举了举,像是在敬某个看不见的对手。
“艾尔肯·托合提。”他轻声念出这个名字,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希望你别让我失望。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比一群乌合之众有趣多了。”
(6)
回到乌鲁木齐,艾尔肯在办公室坐到了晚上十点。
他把古丽娜调出来的所有数据反复看了三遍,在脑子里构建着一张越来越复杂的关系网。境外IP、舆情模型、可疑账号、科技公司……这些碎片像一副被打散的拼图,等待他一块块拼凑起来。
他还没有和林远山汇报阿里木打来电话的事。
不是因为不信任上级,而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想清楚。阿里木说自己“惹上了麻烦”,说需要帮助,说要当面谈——这些话到底是真心求救,还是引他入局的诱饵?十年的空白像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他无法判断沟壑对面站着的,究竟是曾经的朋友,还是陌生的敌人。
手机屏幕亮了。
是前妻热依拉发来的视频:娜扎在医院走廊里蹦蹦跳跳,手里拿着一个棉花糖,对着镜头喊“爸爸,你看我的棉花糖!”
艾尔肯看着女儿的笑脸,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他回复了一条消息:告诉娜扎,爸爸看到了。好好吃,别弄脏衣服。
热依拉很快回了一条:你在忙?
艾尔肯犹豫了一下,打了几个字:嗯,加班。你们早点休息。
然后他放下手机,抬头看向窗外。
远看乌鲁木齐的夜景,灯火万家,每盏灯下都是人,他们过着各自的生活,并不知道这座城市某个角落里正有人和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也不必知道。
这就是隐蔽战线的意义。
守护这些灯火,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发光。
艾尔肯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额头放到冰凉的玻璃上。
父亲的声音又响起,他说儿子守住这片土地不只是扛枪。
“我知道,爸,”他轻声说,“我知道。”
窗外的风向着天山方向飞奔而去,像大地的呼吸一样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