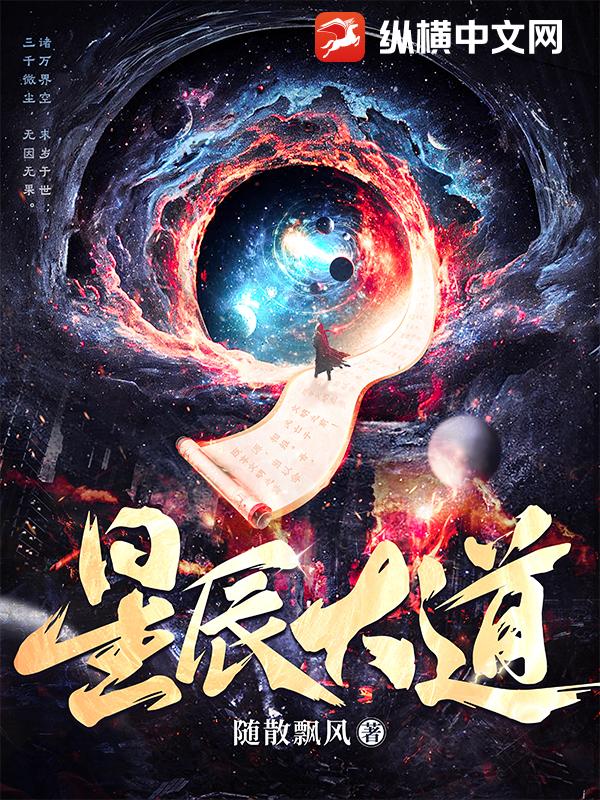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去!为什么不去?!”
许无舟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依旧坐在轮椅上,由漱玉推着,缓缓进入内堂。
脸色在烛火下显得更加苍白虚弱,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带着一种重伤者不该有的、近乎冷酷的清醒。
王伯立霍然转身,苏氏也猛地抬头看向他。
此刻,这位重伤文官成了他们视野中唯一一个似乎还能提出“办法”的人。
“许县令有何高见?”王伯立急问,语气里没了之前的调侃,只剩焦躁。
许无舟咳嗽两声,声音有些沙哑,但逻辑异常清晰:“贼人狡诈凶悍,勒索不断,意在耗尽我等心力财力,更在试探我等底线。然其根本所求,仍是钱财,苏小姐便是他们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他看向苏氏,目光恳切而沉重:“夫人,下官以为,明日黑水潭,赎银照付。不仅要付,还要付得‘干脆’,付得让他们觉得我们已无计可施,只能破财消灾。
此乃稳住贼人,确保苏小姐暂时安全的唯一明路。”
“还要给钱?!”王伯立几乎跳起来,“两万两!下次是不是四万、八万?这何时是个头?!”
“此为一。”许无舟平静地打断他,目光转向墙上地图,“但若只此一路,我等便永是砧板鱼肉。故,必须另辟蹊径,双线并行!”
他手指虚点地图上安平外围几处匪巢:“贼人以此地为凭,嚣张跋扈。我等何不借‘搜寻绑匪同党、探查人质可能下落’之名,行犁庭扫穴之实?王参军可派精锐之师,不纠结于黑水潭一地,而是对这几处为祸最深、最可能与绑匪勾结的匪寨,发动突袭清剿!”
苏氏眼神微动,王伯立也冷静下来,仔细听着。
“此举一可震慑宵小,搅乱山中局势,令贼人外援断绝,耳目失灵;二可制造混乱,逼其转移或露出马脚;三来,”
许无舟声音压低,带着一种引导性的力量,“当周遭匪寨接连被破,那‘吴赐仁’与其同伙,身处惊惶之中,手握‘重宝’却四面楚歌,其心态必然变化。或许,会更急于完成交易,也或许……会在慌乱中犯下致命错误。无论哪种,都比我们只守着一个可能又是陷阱的黑水潭,机会更大。”
王伯立摸着下巴,眼中凶光闪烁:“双线……一边装孙子给钱,一边真刀真枪剿匪?这主意……有点意思!让那帮山耗子首尾不能相顾!”
苏氏权衡着。
继续被动交付巨额赎金,前景渺茫,且屈辱不堪;
而许无舟的提议,虽然冒险,却将主动权夺回了一些,更符合她内心深处想要反击、想要摧毁那些伤害她女儿之人的渴望。
在救女心切的焦灼和巨大的压力下,这个看似激进的方案,成了唯一可选的破局希望。
“便依许县令所言。”苏氏声音冰冷决绝,“伯立,你统筹安排。赎金之事,务必谨慎,以稳住贼人为先。剿匪之师,务必迅猛,以搜寻辛夷线索为要!”
“得令!”王伯立抱拳,重新燃起斗志。这不再是单纯的憋屈交易,而是可以真刀真枪打仗立功的机会!
许无舟适时露出疲惫之色,掩口轻咳:“王参军谋勇双全,必能胜任。只恨下官这副残躯,无法随军效力,阵前杀敌。搜山剿匪,需熟悉当地地理民情之人引导,方能事半功倍。”
王伯立大手一挥:“这好办!你们县衙那个唐浩,不是本地人吗?听说对周边山路匪情门儿清!就让他带路,配合我军行动!”
这正是许无舟想要的结果。他微微颔首,不再多言,只道:“如此甚好。下官便在衙内,尽力为参军协调联络,汇总各方消息,盼早日有好音传来。”
翌日,一切按计划启动。
王伯立一边派出心腹,押送着沉重的“赎银”,战战兢兢地前往黑水潭,另一边,他亲点八百州军精锐,汇合部分本地府兵,在唐浩的引导下,兵分数路,如数柄尖刀,直插安平外围几处主要匪寨。
剿匪的旗号,自然是“搜捕绑匪同党,解救崔氏贵女”。
县衙内,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许无舟以需要“详细了解剿匪进展,以便协调后续”为由,请唐浩出发前尽可能提供更细致的匪寨情报。
这理由合情合理,无人起疑。
待所有棋子都已按照他的预期开始移动,许无舟便以“需与唐捕快家人了解些当地山路旧闻,辅助判断匪情”为借口,只让老黑跟随,悄然来到了唐浩位于县城僻静处的小院。
唐浩家中只有妻子一位,早已被安排妥当。
老黑警惕地守在院门外,许无舟独自一人,推开那扇看似普通的柴房门,顺着狭窄的阶梯,步入了下方阴凉的地窖。
地窖里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暗。角落里,苏辛夷被柔软的布条捆住手脚,靠坐在铺着厚毯的墙边。
她身上换了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裙,发髻散乱,脸上泪痕已干,但眼眶红肿,原本明媚娇艳的脸庞此刻苍白憔悴,嘴唇因缺水而干裂起皮。
她面前摆着的清水和简单饭食,一口未动。
听到脚步声,她猛地抬起头。
当看清来人是许无舟时,她眼中瞬间爆发出极其复杂的光芒——有难以置信,有被背叛的滔天恨意,有深切的恐惧,甚至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残存的、破碎的期待。
许无舟走到她面前几步远停下,沉默地看着她。
地窖里空气凝滞,只剩下油灯灯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
“为什么……”苏辛夷的声音嘶哑得厉害,像是砂纸磨过喉咙,她死死盯着许无舟,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泪般的质问,“许自渡……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的身体微微发抖,不知是冷,还是极致的愤怒与绝望:“那些流萤……烟花……月下的话……都是假的?都是你算计好的?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绑我的人……是你派的,对不对?!”
许无舟静静地承受着她目光的凌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疲惫与暗沉。
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些具体的指控,只是沉默了片刻,迎着她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目光,用平静到近乎残酷的语气,清晰地回答:
“因为我是安平县的父母官。”
这句话像一块冰,砸在苏辛夷沸腾的恨意上,让她猛地一窒。
许无舟继续道,声音在地窖中回荡,低沉而清晰:“安平县内,有被无故围控、生死一线的百姓;安平县外,有盘踞多年、劫掠商旅、祸害乡里的匪患。你的舅舅,手握兵权,盛怒之下,大军若至,玉石俱焚。王参军急躁求功,若只盯赎金,恐激化事端,或徒劳无功。”
他顿了顿,看着苏辛夷眼中变幻的神色,缓缓说出核心:“唯有将水搅浑,将‘营救崔氏贵女’与‘清剿地方匪患’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绑在一起,才能让州军的刀,砍向该砍的地方;才能让所有人的注意力,从城内无辜百姓身上移开;才能有机会……扫清阻碍安平未来的顽疾。”
“所以……我就是你搅浑水的棋子?是你用来调动州军、清理土匪的借口?!”
苏辛夷的声音尖利起来,带着哭腔,更多的是心碎后的冰冷讥讽,“许自渡,你好狠的心!好深的算计!我那么……我那么……”她说不下去了,泪水再次涌出,却是冰冷的。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住更多人的性命,给安平争一个喘息和未来的可能。”许无舟的语气依旧平稳,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至于你,苏小姐,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你性命。待风波过去,时机合适,你自会安全回到你母亲身边。唐浩护你有功,此事过后,州府必有封赏,他在安平也能更稳,不至因秉公办事而遭报复。”
“哈……哈哈……”苏辛夷笑了起来,笑声凄楚而绝望,“为了安平?为了百姓?好冠冕堂皇的理由!许无舟,你不过是个自私冷酷、玩弄人心的骗子!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对你的……”
她咬住嘴唇,将最后那几个字咽了回去,化作更加深刻的恨意,狠狠瞪着他,“我不会原谅你!永远都不会!我舅舅……我母亲……绝不会放过你!”
许无舟静静地听着她的控诉和诅咒,脸上无悲无喜。
直到她喘息着停下,他才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你的恨,我受着。但安平县,不能乱;该做的事,必须要做。”
“呵……呵呵……”
苏辛夷的笑声从凄楚转为一种冰冷的、带着浓浓讥诮的腔调,她抬起泪痕交错的脸,眼神像淬了毒的针,“许无舟,好一个‘父母官’,好一番‘不得不做’的苦心!你以为你赢了?算尽了一切?”
她挣扎着试图坐直,尽管被缚,背脊却挺起一股不肯屈服的倔强:“是,你眼下是绑住了我,用我的‘失踪’,搅动了州军,去清剿那些土匪。你暂时护住了城里那些贱民的性命,没让我舅舅的大军立刻碾过去。可那又怎么样?”
她死死盯着许无舟,一字一句,如同冰锥凿击:“你能绑我一时,还能绑我一世吗?十天?半个月?一个月?我舅舅和王伯立不是傻子!等他们剿光了外围的土匪,却发现根本找不到我,或者找到的线索全都指向死路……他们会怎么想?这游戏,你还能玩多久?”
地窖里的空气仿佛因她的话语而冻结。
油灯的光芒在她眼中跳动,映出一种近乎绝望的清明。
她深吸一口气,抛出了最残忍、也最现实的问题,嘴角勾起一抹近乎恶意的弧度:“除非……你杀了我。死无对证,线索全断。把我埋在某个剿匪的战场下,或者扔进无人知晓的深涧。然后告诉所有人,是穷凶极恶的匪徒‘吴赐仁’撕了票。这样,或许能平息我舅舅的怒火,或许能让我母亲死心,或许……才能真正让你想保护的安平,暂时躲过一劫。”
她紧紧逼视着许无舟,不放过他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可是,许大县令,你敢吗?你这个口口声声为了百姓、不得已而为之的‘父母官’,敢为了你的安平,手上沾上我——一个无辜的、被你欺骗利用的女子的血吗?你的‘必须这么做’,敢做到这一步吗?”
这番话,像最锋利的解剖刀,将许无舟看似环环相扣的计划下,那隐藏的、关于时间、关于后果、关于人性底线的终极困境,血淋淋地剖开,摊在他面前。
绑架是手段,拖延是策略,但所有的算计都建立在苏辛夷最终“活着、安全归来”的基础上。
一旦这个基础动摇,或者对方家族不肯罢休,那么他暂时争取到的一切,都可能化为更猛烈的反噬。
许无舟静静地站在昏暗的光线里,听着苏辛夷字字诛心的质问。
他的脸上依旧没有什么剧烈的表情波动,但那双深潭般的眼眸,瞳孔几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映着跳动的灯焰,更显幽深难测。
胸前的伤口似乎又在隐隐作痛,但他站得笔直。
沉默在地窖中蔓延,只有苏辛夷略带急促的呼吸声。
她在等待,等待这个将她拖入地狱的男人,会如何回答这个关于生死、道德与最终抉择的诘问。
许无舟没有立刻回答。
他缓缓抬起眼,目光再次落在苏辛夷苍白却充满恨意与挑衅的脸上。
那目光复杂至极,有审视,有凝重,有一闪而过的疲惫,但唯独没有恐慌或迟疑。
过了许久,久到苏辛夷几乎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才用那低沉而平稳的声音,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特的重量,砸在凝滞的空气里:
“你说得对。绑架是暂时的,保护也可能是暂时的。杀你……”他顿了顿,目光如古井无波,“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也永远不会是选项。”
说完,他不再看苏辛夷惨然绝望的脸,转身,一步一步,沿着阶梯离开了地窖。
将那片昏暗、压抑、以及一个少女彻底破碎的信任与情愫,留在了身后。
柴房的门轻轻关上,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
许无舟站在院中,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起眼,胸前的伤口又在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