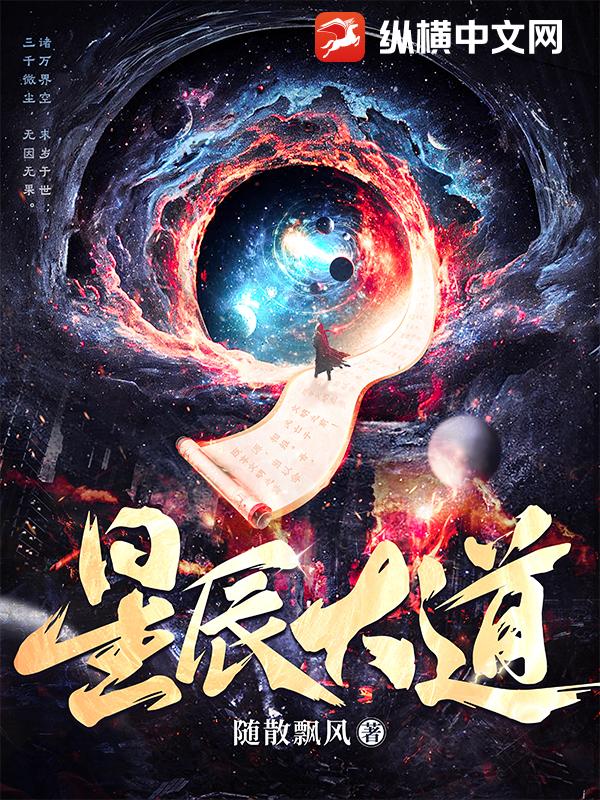福州路17号,废弃泵房的铁门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像是一声压抑在喉咙底的呜咽。
凌晨两点的上海,空气里凝结着黄浦江飘来的湿冷雾气。
苏晚萤关上手电筒,只留指缝间漏出的一丝微光。
这里是法租界的盲区,连流浪猫都嫌弃的死角。
她摸索着那把带着铁锈味的钥匙,插入锁孔。
随着“咔哒”一声轻响,尘封已久的黑暗向她敞开。
泵房内部充斥着霉烂的草席味和机油味。
苏晚萤没有急着深入,而是贴着墙根,每一步都试探着脚下的虚实。
在一个布满蜘蛛网的墙角,水泥缝隙里别扭地塞着一团废纸,似乎是用来堵风口的。
出于职业本能,她抽出那团纸展开。
借着微弱的光,她看清那是一张半残的印刷校对稿——《工务月报》。
苏晚萤的瞳孔猛地一缩。
排版是常见的铅印,但上面的日期赫然印着“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
现在是民国二十五年。
这如果是排版工人的笔误,把“二十一”错拼成了“三十一”,那也错得太离谱了。
更让她背脊发凉的是,被红笔重重圈出的那一段:“……管道渗漏修复工程,谨以此纪念南京沦陷五周年……”
一种荒谬的眩晕感袭来。
这仿佛不是一张废纸,而是一封来自地狱的预告函。
她下意识地将这张纸揉碎,塞进贴身的暗袋。
这不是现在的她能理解的信息,但直觉告诉她,这和沈听澜那个疯子有关。
那个看似纨绔的男人,眼里总藏着某种悲悯的、俯瞰众生的死寂。
清晨六点,金陵东路。
灰白的天色下,暴雨预警的广播还没响,林氏商会的工程队已经拉起了黄黑相间的围挡。
“少爷,公董局那帮洋人还在睡觉,在这个点递交‘暴雨应急路面加固方案’,除了我们也没谁了。”赵承垏打着哈欠,手里依然那把精致的折扇,只是扇面上沾了些晨雾。
沈听澜坐在车里,手里端着一杯刚从路边摊买来的热豆浆。
他没说话,只是透过车窗,看着那几个穿着灰色工装的聋哑工人。
新铺的沥青还在冒着刺鼻的白烟,滚烫,粘稠。
工人们没有用常规的压路机,而是推着一种特制的、底部刻有繁复凹凸纹路的铁滚筒,在尚未凝固的黑色路面上反复碾压。
那些纹路看似是防滑的刻痕,实则是昨夜那枚袖扣里藏着的、731部队冷库通风管道图的拓印。
“这沥青掺了特殊的胶粉。”沈听澜喝了一口豆浆,感受着暖流滑入胃袋,“热胀冷缩后,这些纹路平时看不出来。只有在特定的角度,或者下雨积水的时候,光影折射才会显出原本的脉络。”
他将豆浆杯递给赵承垏,眼神平静得可怕:“我们在给即将入城的‘瞎子’们,铺一条看得见的路。”
上午十点,军统上海站档案室。
苏晚萤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她借着“追查泄露账本的叛徒”的名义,调阅了林氏商会近两个月所有的市政工程报备图纸。
图纸画得很专业,甚至可以说是过于专业了。
每一条管线的走向、每一处承重墙的计算,都透着一股严谨的学院派气息。
她的目光落在图纸右下角的署名上——只有简单的“H.W”两个字母。
苏晚萤翻开了那本积灰的《中央大学教职员名录》。
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最终停留在民国二十七年的一页档案上(此时她并未意识到档案的时间悖论,只当是资料混乱),那个名字让她心头一跳:韩文清,土木工程系助教。
备注栏里用红笔写着三个字:已失踪。
而旁边附带的绝密调查报告显示,此人最后一次出现,是与几名激进学生一同参加抗日救亡游行,极大概率是那个被称作“地下党”的组织发展的技术骨干。
沈听澜……林氏商会……地下党。
这三条线在苏晚萤的脑海中交汇。
她原本以为沈听澜只是个游走在多方势力间谋取私利的投机者,或者是一个只想保全家业的墙头草。
但现在,这个“汉奸”的绘图室里,竟然藏着赤党的技术专家?
中午十二点,沈公馆餐厅。
沈听澜慢条斯理地切着盘子里半熟的牛排,血水渗进白瓷盘的纹路里。
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
“老鼠昨晚烧了窝。”老钟的声音在听筒里显得有些失真,“高雄那边的线人确认,76号焚毁了大部分关于转运站的往来公文。但是……”
沈听澜叉起一块牛肉,停在嘴边:“但是什么?”
“但是关于冷库通风系统的图纸没烧。日本人太傲慢了,他们把那份图纸夹在了‘防疫物资申领单’的附件里,当作普通基建档案归档了。”
沈听澜轻笑一声,将牛肉送进嘴里,优雅地咀嚼,仿佛听到的不是生死攸关的情报,而是今天的天气不错。
“防疫物资?好借口。”他放下叉子,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对站在一旁候命的赵承垏说道,“去,放个风出去。就说我沈听澜最近因为那批被扣的盘尼西林亏了血本,现在跟疯狗一样想咬人。谁要是能提供日本人‘违反防疫条例、私运违禁品’的证据,不管真假,我林家愿意出双倍价钱收购。”
赵承垏眼睛一亮:“少爷这是要逼日本人自己把那张‘防疫单’交出来辟谣?”
“贪婪是最好的催化剂。”沈听澜淡淡地说,“当76号发现一张废纸能换回真金白银的时候,他们会比谁都急着去翻垃圾堆。”
傍晚六点,暴雨如期而至。
苏晚萤再次回到了福州路17号的泵房。这一次,她没有开灯。
在泵房最深处的一块松动的地砖下,她摸到了一个冰冷的金属把手。
用力提起,下面是一个早已干涸的蓄水池,里面赫然放着一台改装过的手摇发电机。
她深吸一口气,握住摇柄,开始匀速转动。
“嗡——”
微弱的电流顺着导线爬升,连接着角落里一颗被黑布蒙住的小灯泡。
灯光透过黑布上的针孔,在这漆黑的地下室里闪烁出断断续续的节奏。
短、短、长……长、短……
摩尔斯电码。
苏晚萤在脑海中迅速译码,随着最后一个信号的熄灭,她的手停在了半空。
只有五个字。
“信你,勿独行。”
这一瞬间,那种长久以来在刀尖上行走的孤独感,仿佛被这微弱的电流击穿了一个缺口。
对方不仅知道她会来,甚至算准了她查到了韩文清的身份后会陷入迷茫和自我怀疑。
这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承诺。
苏晚萤沉默了良久。
她从腰间拔出那把勃朗宁手枪,卸下弹夹,将枪身埋进了蓄水池的淤泥深处。
然后,她站起身,拍了拍旗袍上的灰尘。
这一次,她没有带枪。
她从门后的伞架上拿起一把黑色的长柄雨伞,推开铁门,走进了漫天的大雨中。
雨水冲刷着街道,也冲刷着这座城市表面覆盖的虚伪和平。
午夜将至,雨势并未减弱,反而像是要把整个上海滩淹没。
金陵东路的施工现场空无一人,只有那座高耸的塔吊,像个沉默的巨人,在雷电的闪光中投下巨大的阴影。
沈听澜站在塔吊冰冷的金属爬梯下,仰头望向那没入云端的顶层操作室,雨水顺着他的风衣下摆汇聚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