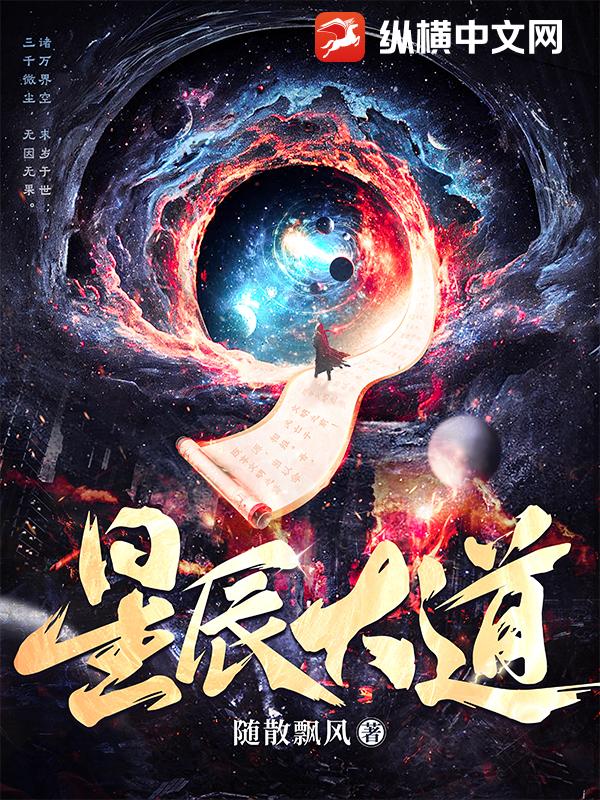南境,禹州首府“南炎府”,平南王府。
正午的烈日炙烤着王府森严的朱漆大门,门前两尊怒目石狮仿佛也被晒得无精打采。然而,王府深处,那座名为“炽焰堂”的书房内,气氛却比烈日更灼人,压抑得令人窒息。
平南王齐炎煌端坐在铺着斑斓虎皮的紫檀木太师椅上,他正值壮年,身材魁梧,一身赤金蟒袍,虬髯戟张,不怒自威。此刻,他浓眉紧锁,铜铃般的眼睛死死盯着站在下首的女儿——郡主齐彤云。
齐彤云一身火红的劲装,勾勒出矫健的身姿,马尾高束,英气逼人。她刚刚结束为期半月的边境巡猎归来,麦色的肌肤上还带着风尘,明亮的眼眸中却燃烧着压抑不住的怒火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
“父王!”齐彤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却异常清晰,“此次巡猎至‘火云涧’,儿臣...儿臣并非只猎得猛兽。儿臣还撞见了一桩事!”
齐炎煌端起手边的冰镇酸梅汤,粗大的指节捏着薄胎瓷碗,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他眼皮微抬,鼻腔里哼出一个沉闷的音节:“嗯?”
“儿臣撞见了一伙人!”齐彤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胸腔里的浊气尽数吐出,“他们打着‘剿匪’的旗号,却行掳掠之事!目标全是...全是十三四岁的少女!手法狠辣,行动诡秘!儿臣亲眼所见,他们将掳来的少女装入蒙着黑布的铁笼马车,往...往‘百越集’的方向去了!儿臣本想追击,却被他们的暗哨发现,交手一番,对方武功路数阴狠刁钻,不似寻常山匪,倒像是...像是合欢派的手段!”她刻意加重了“合欢派”三个字,目光紧紧锁在父亲脸上。
“啪嚓!”
齐炎煌手中的薄胎瓷碗应声而碎,冰凉的酸梅汤混着瓷片溅了他一手,也溅湿了昂贵的虎皮。他猛地站起身,魁梧的身躯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狂暴的气势瞬间充斥整个书房。他额角青筋暴跳,眼神如刀锋般锐利,死死钉在齐彤云脸上。
“混账东西!”一声雷霆般的怒吼炸响,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妄议军务!窥探机密!”
齐彤云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怒震得后退半步,但她倔强地挺直脊梁,毫不退缩:“父王!那不是什么军务机密!那是活生生的人命!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少女何其无辜?她们...”
“住口!”齐炎煌一步踏前,巨大的阴影瞬间笼罩了齐彤云,他蒲扇般的大手高高扬起,带着凌厉的掌风,眼看就要落下!书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侍立在角落的几名亲兵噤若寒蝉,连呼吸都屏住了。
齐彤云闭上了眼睛,紧咬着下唇,准备承受父亲的怒火。然而,那预料中的耳光并未落下。齐炎煌的手掌停在半空,剧烈地颤抖着,最终狠狠攥成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他胸膛剧烈起伏,粗重的喘息如同拉动的风箱。
“彤云...”齐炎煌的声音低沉下来,却带着一种更令人心悸的冰冷,“你是我齐炎煌的女儿!是平南王府的郡主!不是那些悲天悯人的酸腐文人!更不是江湖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侠女’!”
他俯下身,灼热的气息喷在齐彤云脸上,一字一句,如同烧红的烙铁:“南境!是本王的地盘!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兽,都由本王说了算!本王做什么,不做什么,轮不到你来置喙!更轮不到你来‘撞见’!你只需记住你的身份!做好你的郡主!将来寻一门好亲事,相夫教子,延续我齐家血脉!这才是你的本分!”
他猛地直起身,指着书房门口,声音如同寒冰:“滚回你的‘栖霞苑’!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王府半步!再让本王听到你胡言乱语,窥探不该窥探之事...”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家法伺候!绝不轻饶!”
齐彤云猛地睁开眼,那双曾经明亮如火、充满野性与骄傲的眼眸,此刻只剩下无尽的失望、冰冷和一种被彻底背叛的痛楚。她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父亲,看着他脸上不容置疑的威严和眼底深处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心虚?或者说,是某种被触及核心利益后的暴戾?
她最后看了一眼父亲,那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愤怒,有悲伤,有难以置信,最终都化为一片死寂的冰原。她没有再争辩一个字,只是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这书房里令人作呕的空气都吸进肺里,然后猛地转身,大步流星地冲出了炽焰堂。火红的背影在烈日下划出一道决绝的弧线,消失在回廊深处。
齐炎煌看着女儿消失的方向,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烦躁地挥退亲兵,独自在狼藉的书房内踱步。良久,他走到书案前,拿起一份用火漆密封的密函,上面印着一个扭曲的阴阳鱼标记。他眼中闪过一丝挣扎,最终还是将其投入了桌角的火盆。火苗瞬间吞噬了信函,也映照出他眼中复杂难明的光芒——是野心?是无奈?还是对某种不可抗力深深的忌惮?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神州皇城,靖海王府深处。
不同于南境的燥热,这里临海,空气中带着咸湿的水汽。靖海王正妃南宫琉璃的居所“听潮阁”内,却弥漫着一种比海水更沉重的压抑。
南宫琉璃一身素雅的月白宫装,未施粉黛,坐在临窗的软榻上。她面前的小几上,放着一枚小巧玲珑、镶嵌着粉色珍珠的胭脂盒。这本是她小妹南宫明玉最心爱之物。此刻,她纤细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摩挲着胭脂盒冰凉的瓷面,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翻涌的海浪。
贴身侍女碧痕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个密封的蜡丸呈上,低声道:“娘娘,南边来的,‘海鹞鹞’的密报。”
南宫琉璃猛地回神,眼中瞬间爆发出锐利的光芒。她迅速接过蜡丸,捏碎,取出里面卷得极细的纸条。展开,上面只有寥寥数语,却让她本就苍白的脸色瞬间褪尽最后一丝血色,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
“...三小姐...于‘凝香苑’癸字水牢...受尽折磨...元阴几近枯竭...神智时清时昧...恐...恐时日无多...口中唯念‘姐姐’...”
“噗——!”
一口鲜血毫无征兆地从南宫琉璃口中喷出,溅落在月白的宫装上,晕开刺目的猩红。她眼前阵阵发黑,身体软软地向后倒去。
“娘娘!”碧痕惊呼一声,慌忙上前扶住她。
南宫琉璃死死攥着那张染血的纸条,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带来阵阵刺痛,却远不及心中万分之一的痛楚。明玉...她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妹妹!那个笑起来像阳光一样明媚,总爱缠着她撒娇的小妹!竟然...竟然被折磨成这般模样!元阴枯竭?神智不清?时日无多?
蚀骨香!那是极乐宫最阴毒、最残忍的采补邪药!中者如坠地狱,生不如死!她甚至能想象到明玉在那暗无天日的水牢里,承受着怎样的非人折磨!那一声声无意识的“姐姐”,如同最锋利的刀子,一刀刀剜着她的心!
巨大的悲痛如同滔天巨浪将她淹没,但随之而来的,是比巨浪更狂暴、足以焚毁一切的仇恨!她猛地推开碧痕,挣扎着坐直身体,眼中再无半分往日的温婉娴静,只剩下血红的、近乎疯狂的杀意!
“齐!洪!荒!媚!三!娘!”她一字一顿,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名字,每一个字都带着刻骨的怨毒与冰冷的杀机,“我要你们...血债血偿!千倍!万倍!”
她猛地一掌拍在软榻的扶手上,一个隐秘的机括应声而开。暗格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排排整齐的、散发着冰冷寒光的黑色玄铁令箭——靖海王府最隐秘、最强大的力量,“海龙死士”的调兵符!
她抓起一枚令箭,冰冷的触感让她沸腾的血液稍稍冷却,但眼中的火焰却燃烧得更加炽烈。她看向碧痕,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传‘海龙令’!”
“目标:神州皇城,极乐宫总坛‘海蜃楼’!”
“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焚毁‘海蜃楼’!诛杀媚三娘!若遇皇帝爪牙阻拦...杀无赦!”
“时限:三日!”
“执行者:海龙死士,全体!”
“此令...绝密!绝杀!绝后!”
碧痕接过那枚沉甸甸、仿佛带着血腥气的令箭,感受到其上几乎凝成实质的杀意,身体微微一震,随即眼中爆发出同样决绝的光芒:“属下领命!海龙所至,鸡犬不留!”
碧痕的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南宫琉璃瘫软在软榻上,看着宫装上刺目的血迹,仿佛看到了小妹苍白痛苦的面容。她抓起那枚小小的胭脂盒,紧紧攥在手心,冰凉的瓷片硌得生疼,却让她混乱的心神有了一丝奇异的清明。
“明玉...再等等姐姐...”她低声呢喃,声音如同来自九幽深渊,“姐姐...这就去把那座魔窟...连同里面的魔鬼...一起...烧给你看!”泪水无声滑落,滴在胭脂盒上,与那抹刺目的血迹融为一体。靖海王府的怒火,化作焚海之龙,无声无息地潜入了波涛汹涌的皇城暗流之中。
神州皇城,御书房。
浓烈的龙涎香混合着丹药的甜腻与淫靡气息,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味。齐洪荒赤着上身,披头散发,双目赤红如同滴血,在铺着白虎皮的软榻上烦躁地翻滚。他刚刚服下一颗“冰肌玉骨丹”,药力带来的冰火交织的快感与内心的暴戾焦躁交织在一起,让他如同困兽。
“废物!一群废物!”他抓起一个玉镇纸狠狠砸向墙壁,碎片四溅!“夜玄!朕的‘神女丹’主材呢?!师妃暄!詹台璇!那两个贱人到底躲到哪里去了?!还有查封帝踏峰的事!冷青崖是吃干饭的吗?!”
夜玄垂首立于阴影中,面具下的声音带着诡秘的平静:“陛下息怒。追魂索魄之术已锁定慈航静斋方向,师妃暄与那白衣女子必在帝踏峰附近!冷都统已调集玄衣卫精锐与肃政台高手,三日后子时,必能攻破帝踏峰山门,擒拿所有静斋弟子!届时,以静斋弟子为饵,不愁师妃暄不现身!”
媚三娘扭着水蛇腰上前,娇躯紧贴齐洪荒,声音甜腻如蜜:“陛下~何必心急?帝踏峰那群尼姑,元阴纯净,可是上好的‘辅药’!待擒下她们,正好为陛下炼制一批‘清心玉露丹’,固本培元~至于师妃暄和詹台璇…”她眼中闪过贪婪与怨毒,“只要她们敢来,妾身与阴阳阁主、合欢宗主联手布下的‘三才锁仙阵’,定叫她们插翅难飞!届时,抽其元阴,炼其剑魄,必能成就陛下无上神丹!”
齐洪荒闻言,眼中暴戾稍减,贪婪的红光再次亮起:“好!好!三日后!朕要亲眼看着帝踏峰化为焦土!看着那群假清高的尼姑跪地求饶!至于师妃暄和詹台璇…”他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朕要活的!朕要亲手...把她们炼成丹!”
他一把将媚三娘拉入怀中,大手在她身上肆意揉捏,淫笑道:“爱妃立此大功,朕定要好好‘赏’你!待神丹炼成,朕与你...共享长生!哈哈哈哈!”
夜玄面具下的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共享长生?愚蠢!他要的,是那白衣女子身上纯净的月华本源!待阵法发动,趁乱夺取,这疯帝和这些邪魔...不过是他的垫脚石!他悄然退入更深的阴影,如同等待猎物的毒蛇。
栖霞苑。
齐彤云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背靠着冰冷的门板,缓缓滑坐在地。门外传来侍女小心翼翼的询问声,被她粗暴地喝退。父亲的怒吼、那铁笼马车里隐约传来的少女啜泣、以及墨浅讲述的边境惨状,如同走马灯般在她脑海中疯狂闪现。
她猛地站起身,冲到妆台前,看着铜镜中自己苍白而愤怒的脸。她一把抓起妆台上那些华贵的珠钗首饰,狠狠摔在地上!珍珠翡翠滚落一地,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她扯下头上的金步摇,连同束发的玉簪,狠狠掷向墙壁!仿佛要将这身代表平南王府郡主的枷锁彻底砸碎!
“身份?本分?”她对着镜子冷笑,眼中是燃烧的火焰,“去他的郡主身份!去他的相夫教子!”
她走到窗边,猛地推开窗户。南炎府午后的热浪扑面而来,带着市井的喧嚣。她的目光越过王府高耸的围墙,投向南方莽莽群山的方向。那里,是百越族的聚居地,也是墨浅和她那些“义从军”伙伴活跃的地方。
不能再等了!父王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不仅是知情者,更是参与者!这王府,这看似尊贵的身份,早已成了禁锢她的囚笼,甚至可能成为她良知的绞索!
她迅速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素笺,提笔疾书。笔锋凌厉,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墨浅吾友:”
“王府一晤,心已寒彻。父非吾父,家非吾家。所见所闻,污浊不堪,令人发指!彤云虽为女流,亦知大义所在,羞与此辈为伍!”
“今决意弃此樊笼,投身光明。愿效犬马之劳,随君左右,涤荡妖氛,还南境清明!三日后子时,南城外‘望乡亭’,盼君相候,共谋大事!”
“切切!彤云泣血顿首”
写完,她吹干墨迹,小心折好。她没有唤王府的侍女,而是走到窗边,对着庭院角落一株茂盛的芭蕉树,学了三声清脆的鹧鸪鸟鸣。片刻后,一个穿着王府杂役服饰、面容普通的少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窗下。
“小石头,”齐彤云将信笺递出窗外,声音压得极低,眼神却无比锐利,“老规矩,用‘飞羽’渠道,务必亲手交到墨浅姑娘手中!绝密!速去!”
少年小石头接过信笺,重重点头,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庭院深处,仿佛从未出现过。他是齐彤云多年前一次狩猎时救下的孤儿,一直被她秘密培养,是她在这看似铁桶般的王府中,唯一完全信任的暗线。
做完这一切,齐彤云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她走到床边,从枕下摸出一把造型古朴、带着南蛮风格的锋利匕首——这是她十五岁生辰时,父王亲手所赠,祝贺她第一次独立猎杀了一头成年花豹。她曾视若珍宝。
她抽出匕首,冰冷的寒光映照着她决绝的脸庞。她走到书案前,拿起那份记录着“剿匪”缴获物资(实为掳掠少女)的卷宗副本——这是她费尽心机才从父亲书房里偷偷抄录的罪证。
匕首的锋刃,毫不犹豫地划破了卷宗,也划破了父女之间最后一丝温情。
“父王...”她低声自语,声音冰冷如铁,“这条路,是您逼我选的。”
她将划破的卷宗凑近烛火。火苗瞬间窜起,贪婪地吞噬着纸张,也吞噬着那个曾经天真骄傲、只知骑马射猎的平南郡主。火光跳跃,映照着她眼中再无半分迷茫、只剩下焚尽污浊的熊熊烈焰。
栖霞苑的窗外,烈日依旧灼人。而一场席卷南境的风暴,已在无声中酝酿成型。平南王府的郡主,于此刻,正式点燃了反叛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