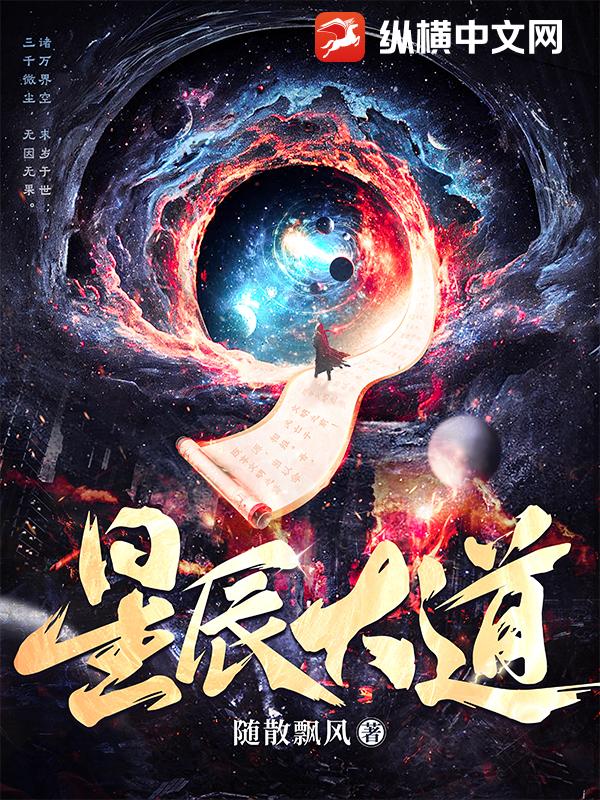奏章递上去的第三日,相邦府送来了请柬。
鎏金的木牍上,吕不韦的亲笔字迹工整有力:“闻君高论,颇有所得,今夜酉时,寒舍略备薄酒,望嫪先生拨冗一叙。”
先生。
这个称呼让白斟时眯起了眼。
在秦国,能被称为“先生”的,要么是名动天下的学者,要么是诸侯座上宾的谋士。
吕不韦用这个词,既是抬举,也是试探,他想看看,这个甘泉宫的面首,曾是他的门客,到底有几分真才实学。
“要去吗?”
赵太后把玩着请柬,语气听不出喜怒。
“相邦相请,不敢不去。”
白斟时恭敬道,“只是臣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这宴无好宴。”
白斟时实话实说,“臣的奏章,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反对修渠的朝臣、靠赈灾捞钱的官吏、甚至……可能包括相邦本人。”
赵太后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冷意:“你倒是清醒,不过毐郎,你要记住,在这咸阳城里,敢动哀家的人,还没出生。”
她起身走到白斟时面前,抬手替他整理衣领。
这个动作很亲昵,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他的脖颈,最后划向小腹……
“换上那套月白深衣,哀家前日赏你的,要让吕不韦看看,甘泉宫出去的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比的。”
白斟时垂眸:“诺。”
指尖的触感温热,带着淡淡檀香,他能感觉到赵姬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
那目光里有欣赏,有占有,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早点回来。”
赵太后最后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哀家……等你。”
酉时初,白斟时乘着甘泉宫的马车,驶向相邦府。
车厢里,他闭目养神,脑海中飞速复盘所有可能的情况,吕不韦的宴请无非几种目的,拉拢、试探、敲打,或者……设局。
马车忽然一顿。
“怎么回事?”白斟时掀开车帘。
车夫是黑夫安排的自己人,此刻压低声音道:“主子,前面桥头有人设卡,说是查盗匪。”
渭水桥,白斟时心头一凛,这是去相邦府的必经之路。
此时天色已暗,桥头火把摇曳,映出七八个黑衣人的身影,看装扮像是官差,但站姿仪态……
不对。
“掉头。”白斟时当机立断。
几乎在同一瞬间,那伙人动了。
为首的汉子一声呼哨,七八人同时拔刀扑来,动作迅猛狠辣,绝不是什么寻常官差!
“驾!”
车夫猛抽马鞭,马车一个急转,车轮在青石路上擦出刺耳声响。
但已经晚了,两个黑衣人从侧面屋檐跃下,刀光直劈车厢!
白斟时侧身翻滚,刀锋擦着肩膀划过,深衣被划开一道口子。
他顺手抓起车厢里的铜制香炉,狠狠砸向最近那人的面门。
“砰!”
一声闷响,那人踉跄后退。
但更多的人围了上来,刀光在暮色中交织成网,车夫已中刀倒地,马匹受惊嘶鸣。
白斟时背靠车厢,呼吸急促,前世他练过几年格斗,但面对这种真刀真枪的围攻,那点技巧根本不够看。
要死在这里?
这个念头刚闪过,桥的另一端忽然传来急促马蹄声。
“何人胆敢在咸阳行凶!”
一声厉喝,如惊雷炸响,紧接着箭矢破空,冲在最前的两个黑衣人应声倒地。
白斟时抬眼望去,只见一队黑衣玄甲的骑兵如黑色洪流涌上桥头,为首者是个年轻将领,面如冠玉,目若朗星,手中长弓还未放下。
“蒙恬在此,贼子受死!”
蒙恬!
白斟时心中一震,未来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的秦国名将,此刻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将领。
黑衣刺客见势不妙,一声呼哨,迅速撤退,几个起落便消失在暮色中。
蒙恬策马上前,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车夫,又看向白斟时:“阁下没事吧?”
“多谢将军相救。”
白斟时拱手,肩上的伤口此时才传来刺痛,鲜血已浸透月白深衣。
蒙恬下马,走近仔细看了看他的伤口:“皮肉伤,无大碍。”
他的目光在白斟时脸上停留片刻,“阁下是……甘泉宫的嫪内侍?”
“将军认得我?”
“太后身边的新晋红人,咸阳城里谁不认得。”
蒙恬语气平淡,听不出褒贬,“只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对太后的人动手。”
他蹲下身检查刺客尸体,从其中一人怀中摸出一块木牌。
借着火把光,能看到木牌上刻着一个模糊的印记,像是某种图腾。
蒙恬的眉头皱了起来。
“将军认识这个印记?”白斟时问。
蒙恬沉默片刻,将木牌收起:“此事我会查清,嫪内侍还要去相邦府?”
“宴约在身。”
“我送你。”
蒙恬翻身上马,“正好,我也要去相邦府一趟。”
有蒙恬护送,接下来的路再无波折。但白斟时心中疑云更重,那些刺客训练有素,撤退有序,绝非寻常匪类。
而蒙恬看到木牌时的反应……难不成是秦国老世族……
有意思。
相邦府灯火通明。
吕不韦亲自站在府门前相迎,见到白斟时肩上的伤,故作惊讶:“嫪先生这是……”
“路上遇到些小麻烦,幸亏蒙恬将军相救。”
白斟时微笑,仿佛刚才的生死搏杀只是小事一桩。
吕不韦深深看了他一眼,又看向蒙恬:“蒙将军也来了,正好,宴席刚开。”
宴设在中庭,水榭曲廊,丝竹声声。
席间已坐了十几人,有朝中官员,也有吕不韦的门客,白斟时一眼就看到了李斯,坐在末席,正低头饮酒,仿佛对周遭一切漠不关心。
“嫪先生请上座。”
吕不韦引他到右侧首座,这个位置仅次于主人席,惹得席间不少人侧目。
酒过三巡,客套话说尽,终于有人发难。
“听闻嫪先生前日上了道奏章,主张续修郑国渠。”
说话的是个四十余岁的官员,面白无须,眼神锐利。
“先生可知,那郑国乃是韩谍?修此渠,耗我大秦国力,正是韩国的毒计!”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白斟时。
白斟时放下酒杯,不慌不忙:“敢问这位大人,修渠耗国力,那不修渠,今年大旱,百姓饿死,田亩荒芜,算不算耗国力?”
那官员一愣:“这……”
“耗与不耗,要看产出。”
白斟时继续道,“若耗费百万金,只得一条水渠,那是耗,但若耗费百万金,得关中千里沃野,得万民温饱,得大秦十年粮仓充盈,这还叫耗吗?”
他环视席间:“这叫投资。”
“投资?”有人疑惑。
“投之以资,报之以利。”白斟时解释,“就像商人做生意,本钱投下去,为的是赚更多的钱,修渠的本钱投下去,为的是大秦千秋万代的粮仓。”
李斯忽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吕不韦抚须微笑:“嫪先生高见。只是这修渠之事,牵涉甚广,朝中反对者众,先生可有对策?”
“对策很简单。”
白斟时淡淡道,“让反对的人,去修渠。”
满座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