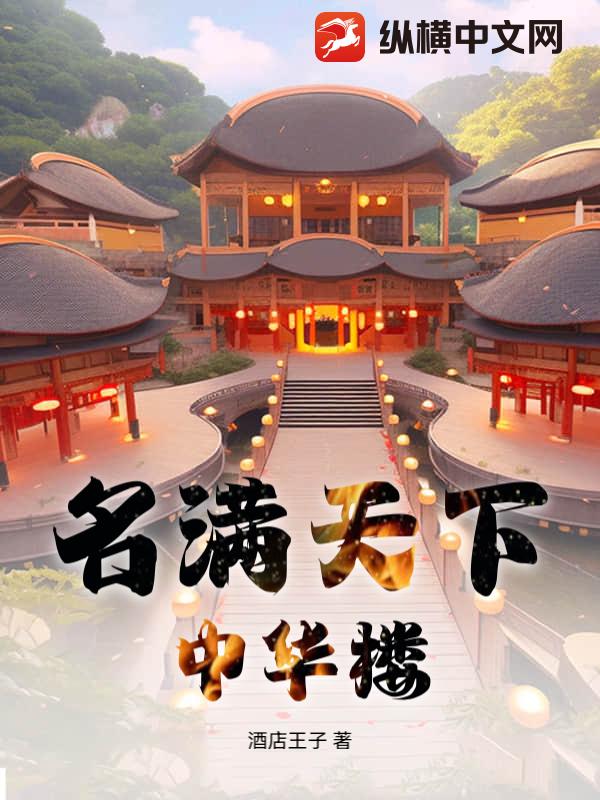腊月二十二,小年夜的前一天,京城迎来了今冬最大的一场雪。
雪花从午后开始飘落,到黄昏时已积了半尺厚。整座京城银装素裹,长安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都缩着脖子匆匆往家赶。唯有中华楼门前的灯笼早早亮起,在风雪中摇曳着温暖的光。
楚云澜站在二楼窗前,望着漫天飞雪,手中捧着一只暖炉,却觉得心口比指尖更冷。
林惊鸿已经离开整整四十九天了。
四十九天前,他接到一封信后便匆匆离去,只留下一句“去查些旧事,少则半月,多则月余便回”。如今四十九天过去,音讯全无。杜清风派人四处打听,只知他去了北疆方向,之后便如石沉大海。
“东家,天冷了,喝碗热汤吧。”李管事端着一碗鸡汤进来,见她仍站在窗前,轻叹一声,“林教头武功高强,定会平安归来的。”
楚云澜接过汤碗,勉强笑了笑:“我知道。只是这雪下得太大,北疆那边怕是更冷。”
她转身看向桌上的沙漏——这是林惊鸿临行前送她的,说沙子漏尽时他便回来。如今沙漏已翻过三次,沙子又快见底了。
“楼里今日生意如何?”楚云澜强打精神问道。
“客人都被大雪困在家里,只来了三桌熟客。”李管事回道,“倒是后院的学徒们听说东家心情不佳,特意酿了一坛‘暖冬酒’,说是等林教头回来时喝。”
楚云澜心中一暖。醉翁学堂如今已有百余学徒,这些年轻人虽不知林惊鸿为何离去,却能体察她的忧心。
“告诉他们,有心了。”她顿了顿,“今晚打烊后,让大家都到前厅来,咱们也过个小年。”
夜色渐深,雪却越下越大。楚云澜裹了件狐裘,提着一盏琉璃灯,独自往后院酒窖走去。
酒窖里温暖如春,数百个酒坛整齐排列。最深处,有一排特殊的酒坛,封泥上刻着日期——那是她和林惊鸿每年冬至封存的“岁寒酒”,约定将来一起品尝。
楚云澜走到最新的一坛前,封泥上刻着“天佑二十二年冬至”。这是林惊鸿离开前三天封的,那时他还笑着说:“等明年开春,这酒正好醇厚,咱们坐在杏花树下喝。”
她轻轻拂去坛上薄尘,忽然听到窖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谁?”楚云澜警觉地转身。
窖门被推开,杜清风披着一身雪进来:“师姐,是我。”他面色凝重,“刚收到北疆传来的消息。”
楚云澜的心提了起来:“可是惊鸿有消息了?”
杜清风点头又摇头:“有人在北疆苍云山下见过他,但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之后他便往雪山深处去了,再无人见过。”
“雪山深处...”楚云澜脸色发白,“这个时节进雪山,他疯了不成?”
“师姐莫急。”杜清风忙道,“林兄行事向来稳妥,既敢进山,必有把握。我猜测,他定是查到了与楚家旧案或幽冥教相关的线索。”
楚云澜沉默片刻,忽然问:“清风,你可还记得,当年我父亲是在何处遇害的?”
杜清风一怔:“不是在京城郊外吗?”
“那是官方的说法。”楚云澜走到酒架旁,取出一只陈年酒坛,拍开封泥,从中取出一卷用油布包裹的纸张,“父亲真正的遇害地,在北疆雪山。这是他当年最后一封密信中透露的,信中说‘若有不测,当往雪山寻迹’。”
她展开油布,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地图,绘着雪山地形,其中一处用朱砂标记。
“这个秘密,我只告诉过惊鸿。”楚云澜的手指轻触那个标记,“他定是发现了什么,才会冒险进山。”
杜清风倒吸一口凉气:“师姐为何不早说?我可以派人...”
“因为父亲在信中说,此事凶险,非必要不可涉足。”楚云澜闭上眼,“我以为惊鸿只是去北疆查些边贸线索,没想到...”
话音未落,前厅突然传来喧哗声。两人对视一眼,快步赶去。
前厅里,三个满身雪花的北狄汉子正在与伙计争执。为首的是个独眼大汉,操着生硬的汉语:“我们只要酒,不要钱!拿酒来!”
李管事试图解释:“客官,本店打烊了,明日请早...”
“打烊?”独眼大汉一掌拍在桌上,木桌应声而裂,“老子从北疆跑到这里,就为喝一口中华楼的酒!今日喝不到,拆了你这破楼!”
楚云澜稳步上前:“三位远道而来,想要什么酒?”
独眼大汉上下打量她:“你就是楚东家?听说你们有种‘岁寒酒’,给老子来三坛!”
楚云澜神色不变:“岁寒酒是私藏,不对外售卖。不过三位既然从北疆来,我请三位喝北狄奶酒改良的‘融冰酒’,如何?”
“谁要喝那种娘们酒!”另一个北狄汉子嚷道,“我们要岁寒酒!听说那酒能暖透冰封的心,老子倒要试试!”
这话说得古怪。楚云澜心中一动,细细打量三人。他们虽作北狄打扮,但靴子是中原样式,手上虎口有厚茧,是长年用剑留下的。
“三位不是北狄人吧?”她忽然道。
三人脸色微变。
楚云澜继续道:“岁寒酒确能暖身,但更需要暖心之人共饮。三位若是真心求酒,不妨说说,为何非要岁寒酒不可?”
独眼大汉沉默片刻,忽然从怀中掏出一物,放在桌上。
那是一枚熟悉的剑穗,青丝编成,坠着一颗墨玉——正是林惊鸿剑上的饰物。
楚云澜瞳孔骤缩:“你们把他怎么了?”
“楚东家放心,林教头安然无恙。”独眼大汉的声音忽然变得清晰流畅,“我们是受他所托,前来报信的。”
他扯下脸上的假胡须,露出一张清秀的脸——竟是个年轻女子。另外两人也除去伪装,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在下柳无痕,这两位是我的师弟。”女子抱拳道,“我们是‘雪山剑派’的弟子,半月前在雪山中遇险,幸得林教头相救。他助我们脱困后,托我们带信给楚东家。”
楚云澜急问:“他为何不自己回来?”
柳无痕神色凝重:“林教头在雪山深处发现了一处幽冥教旧址,其中可能有楚家旧案的线索。他说要深入查探,让我们先带信回来。”她从怀中取出一封蜡封的信,“他说,若一个月后他未归,再请楚东家看信。”
楚云澜接过信,信封上确是林惊鸿的字迹:“云澜亲启”。
“他现在何处?具体位置?”杜清风追问。
柳无痕摇头:“那地方隐秘,我们只知在‘鹰愁涧’附近。林教头说,若他回不来...请楚东家不要去找他。”
“荒唐!”楚云澜握紧信笺,“我怎能不去?”
她当即转身:“清风,准备车马,我要去北疆。”
“师姐,此刻大雪封路,至少要等雪停...”
“等不了。”楚云澜眼中含泪,“他既托人带信,说明情况已十分危险。我必须去。”
柳无痕忽然道:“楚东家若要去,我们带路。雪山地形复杂,没有向导寸步难行。”
楚云澜深深看她一眼:“多谢。”
当夜,中华楼灯火通明。楚云澜将楼中事务托付给杜清风和李管事,又召来众学徒,交代醉翁学堂的事宜。
“东家,让我们跟你去吧!”几个年轻学徒请缨。
楚云澜摇头:“你们留下,好生照看酒楼和学堂。这是我与惊鸿的私事,不该牵连大家。”
她走到金石碑前,抚摸着那些历经风霜的刻字,轻声道:“前辈,您说楼之魂在人心。如今惊鸿有难,我必去寻他。若我们回不来...这楼,就托付给您留下的精神了。”
石碑静默,唯有雪花落在上面,瞬间融化,如泪痕。
子时,雪势稍减。楚云澜带着柳无痕三人,驾着两辆马车悄然出城。车厢里装满了御寒衣物、药材、干粮,还有几坛酒——岁寒酒,以及各种救急药酒。
马车在雪夜中艰难前行,车轮轧过积雪,发出嘎吱声响。楚云澜掀开车帘,回望渐行渐远的京城灯火,心中默默祈祷。
车行三日,方出京畿。越往北,雪越深,路越难行。第四日黄昏,一行人抵达北疆第一镇——寒山镇。
镇子不大,只有一条主街,客栈也仅有一家。掌柜是个满脸风霜的老者,见他们深夜投宿,不免诧异。
“这么冷的天,几位这是要去哪儿?”老者一边登记一边问。
“去鹰愁涧。”柳无痕答道。
老者笔尖一顿,抬头打量他们:“鹰愁涧?这季节去那儿,不要命了?”
楚云澜问:“老丈何出此言?”
“那地方邪门得很。”老者压低声音,“常年雾气笼罩,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出不来。本地人都说,那里住着雪妖,专抓过往行人。”
柳无痕的师弟忍不住道:“我们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老者惊讶地看了他们一眼,不再多言,递过钥匙:“二楼左转,三间房。热水一会儿送上。”
房间简陋,但还算干净。楚云澜推开窗,寒风夹杂着雪粒扑面而来。远处,连绵的雪山在暮色中如巨兽蛰伏,最高处隐在云层里,看不真切。
那就是鹰愁涧的方向。
“楚东家,早些休息吧。”柳无痕在门外道,“明日要赶早进山。”
楚云澜应了一声,却毫无睡意。她取出林惊鸿的信,烛光下,蜡封完好。她几次想拆开,又强忍住——他说一个月后未归再看,她信他。
“惊鸿,你一定要等我。”她对着雪山方向,轻声说。
第五日清晨,一行人换上厚实皮袄,将马车寄存在客栈,改用雪橇和雪鞋进山。柳无痕熟悉地形,带他们走了一条近道,但山路陡峭,积雪及腰,走得极为艰难。
到了午后,楚云澜体力已有些不支。她咬着牙,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脑中却不断闪过与林惊鸿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初次相见时,他一身黑衣站在雨中,说愿做她的护卫;楼宇重建时,他彻夜守在工地,只为护她周全;金石碑前,他说“碑或许会风化,但人心中的记忆永存”...
“楚东家,小心!”柳无痕忽然拉了她一把。
楚云澜回过神,发现前面是一条冰裂缝,宽约丈余,深不见底。若不是柳无痕及时拉住,她已跌入其中。
“此处已是鹰愁涧外围。”柳无痕指着前方,“再往里走,雾气会越来越浓,大家用绳索连在一起,免得走散。”
众人依言用绳索系在腰间,连成一串,继续前行。果然如老者所说,越往里走,雾气越重,十步之外便看不清人影。更诡异的是,雾气中隐隐有呜咽之声,如泣如诉。
“是风声穿过岩缝。”柳无痕解释,但她的手已按在剑柄上。
又走了约一个时辰,前方出现一片冰林。无数冰柱从地面耸立,高矮不一,在雾气中如鬼影幢幢。柳无痕停下脚步,脸色发白:“不对...我们上次来时,这里没有冰林。”
“迷路了?”楚云澜心中一沉。
柳无痕仔细辨认方向,忽然指着一根冰柱:“看那里!”
冰柱中,冻着一只剑穗——与林惊鸿的那只一模一样。
楚云澜冲过去,想要取出剑穗,却发现冰柱坚硬如铁。柳无痕拔剑欲劈,剑锋砍在冰上,只留下一道白痕。
“这冰不对。”她皱眉,“普通冰不会这么硬。”
楚云澜忽然想起什么,从行囊中取出一小坛酒:“用这个。”
“酒?”
“这是‘烈火酿’,酒性极烈,可融坚冰。”她将酒倒在冰柱根部。果然,酒液所到之处,冰层迅速融化,冒出丝丝白气。
片刻后,剑穗露出。楚云澜小心取出,发现下面还冻着一张小纸条。她化开冰层,展开纸条,上面是林惊鸿匆匆写下的字迹:
“雾中有阵,循笛声可破。我在涧底,安。”
“笛声?”众人侧耳倾听,雾气深处,果然传来若有若无的笛音,旋律古朴,正是醉翁散人最爱的《梅花三弄》。
楚云澜眼中一亮:“是惊鸿!他在用笛声指路!”
众人循声而行,笛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引领他们在冰林中穿梭。走了约莫半个时辰,雾气渐散,眼前豁然开朗——一道深涧横亘在前,涧底云雾缭绕,深不见底。
笛声正从涧底传来。
“他在下面。”楚云澜探头望去,只见峭壁如削,根本没有路。
柳无痕查看地形后,指着左侧:“那边有藤蔓,可以攀下去。”
藤蔓粗如儿臂,覆着冰雪,滑不留手。楚云澜却毫不犹豫,抓住藤蔓就往下爬。柳无痕想阻拦已来不及,只得跟上。
下行数十丈,雾气又起。但这次笛声很近,几乎就在耳边。楚云澜加快速度,终于,双脚触到实地。
涧底竟别有洞天。一片温泉冒着热气,周围长着不畏严寒的绿草,甚至还有几株红梅傲雪绽放。温泉旁,一个简陋的草棚里,林惊鸿正倚壁而坐,手中握着一支竹笛。
他衣衫破烂,面色苍白,左臂缠着布条,渗出血迹。但看到楚云澜时,眼中瞬间亮起光芒。
“云澜...”他声音沙哑,“你还是来了。”
楚云澜冲过去,跪在他身边,想碰他又怕弄疼他:“你伤得重不重?怎么不回去?”
林惊鸿握住她的手:“伤不重,只是中了埋伏,被困在此处。”他看向柳无痕三人,“多谢你们带她来。”
柳无痕抱拳:“林教头救命之恩,自当回报。”
楚云澜检查他的伤势,发现除了左臂剑伤,还有几处冻疮。她取出药酒,小心为他处理伤口,又喂他喝了些热酒。
“你发现了什么?”她问。
林惊鸿示意她看草棚内壁。石壁上刻满壁画和文字,虽已斑驳,仍能辨认。楚云澜凑近细看,越看越心惊——壁画描绘的正是十五年前楚家遇害的场景,而文字记载的,是一个惊天秘密。
“当年杀害楚家的,不是幽冥教,也不是幽王。”林惊鸿缓缓道,“而是一个叫‘冰魂’的组织。他们专为权贵处理隐秘之事,楚家灭门,是因为你父亲查到了某个大人物的罪证。”
“谁?”
林惊鸿指向壁画一角,那里刻着一个模糊的徽记——龙纹环绕着一柄剑。
“这是...皇室的暗卫标志?”楚云澜难以置信。
“更准确地说,是先帝私人的暗卫组织。”林惊鸿道,“你父亲查到的罪证,涉及先帝晚年的一桩丑闻。为了掩盖真相,先帝命‘冰魂’灭口。”
楚云澜跌坐在地,浑身冰冷。她想过无数种可能,却从未料到,仇人竟是已故的先帝。
“这些壁画,是谁刻的?”她颤声问。
“应该是当年参与行动、后来良心发现的人。”林惊鸿指着壁画末尾几行小字,“刻者说,他将真相留在此处,希望有朝一日能大白于天下。但他也警告,冰魂组织仍在活动,首领代号‘雪公子’,身份成谜。”
柳无痕忽然道:“雪公子...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师父曾说,北疆有个神秘人物,常在雪山出没,剑法极高,人称‘雪中公子’。”
林惊鸿点头:“我也怀疑,雪公子就是冰魂现任首领。我在此处被困,就是因为发现了他的踪迹,被他的人伏击。”
“你见到他了?”
“只见到背影,白衣如雪,轻功极高。”林惊鸿回忆道,“他留下话说,若我肯放弃追查,可放我生路。我说不可能,他便设阵困我于此,说让我‘冷静冷静’。”
楚云澜握紧他的手:“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现在走不了。”林惊鸿苦笑,“涧底唯一的出路被雪崩封死了。我在此等了一个月,才等到你们。”
柳无痕查看出路后,回来摇头:“确实被封得严实,至少要等开春雪化。”
楚云澜却笑了:“无妨。有温泉,有存粮,还有酒。咱们就在这儿过冬。”
她打开行囊,取出那坛岁寒酒:“今年冬至的酒,咱们提前喝。”
酒坛开启,醇香四溢。五人围坐在温泉边,以雪水煮酒,就着干粮,竟吃出了一番风味。洞外风雪呼啸,洞内却暖意融融。
夜深时,柳无痕三人睡了。楚云澜依偎在林惊鸿肩头,望着洞顶冰棱折射的月光。
“惊鸿,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林惊鸿轻抚她的发:“傻话。为你,值得。”
“等出去了,我们回中华楼,把生意做得更大,把学堂办得更好。”楚云澜眼中闪着光,“然后...我们把婚事办了吧。”
林惊鸿身体一僵,低头看她:“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成亲吧。”楚云澜抬头,眼中含泪带笑,“人生苦短,我不想再等了。无论仇人是谁,无论前路多难,我想和你一起面对。”
林惊鸿紧紧抱住她,声音哽咽:“好。等回去,我们就成亲。”
温泉汩汩,雪光映着洞内一对相拥的身影。洞外,风雪依旧,但涧底这片小小天地里,春天仿佛已提前到来。
而在他们看不见的雪山之巅,一个白衣人静静伫立,望着涧底微光,面具下的唇角,勾起一抹难以捉摸的笑。
“楚云澜...你终于来了。”
他转身,消失在风雪中,只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很快就被新雪覆盖。
夜还长,雪还在下。但归人已寻到,温酒正暖,前路虽险,携手同行便无所畏惧。
中华楼的灯,总会有人点亮。雪夜的酒,总会有人温热。而等待的人,终会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