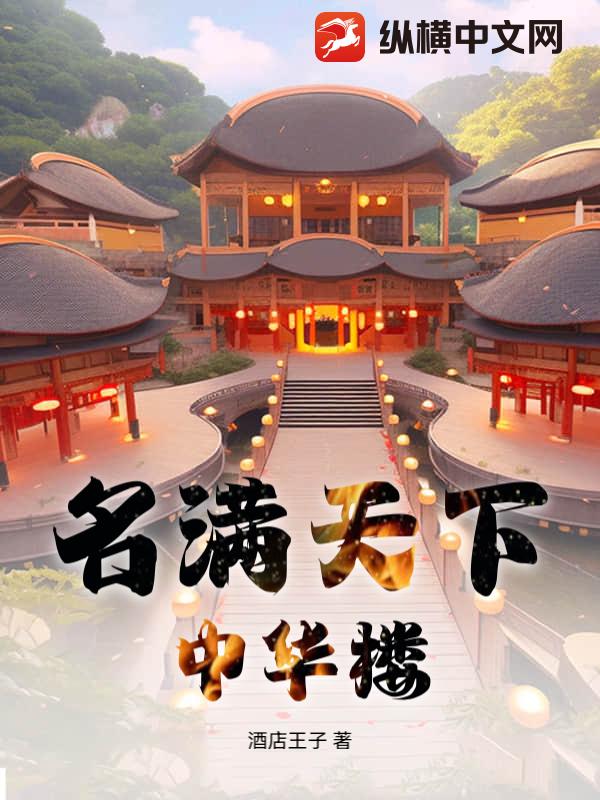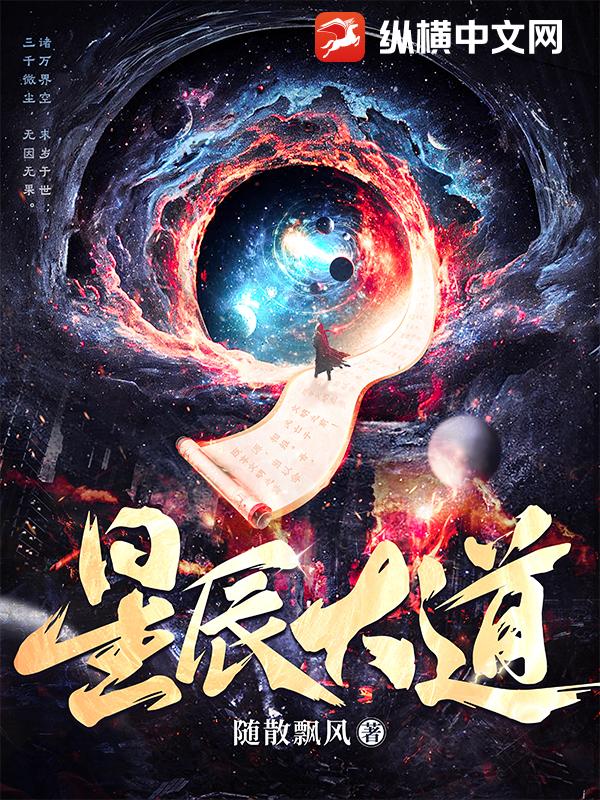秋分过后,京城的天空澄澈如洗。中华楼后院那株百年银杏,叶子已染上浅浅的金黄。楚云澜站在树下,手中捧着一封请柬,眉头微蹙。
请柬是“文渊阁”送来的,邀她三日后参加“天下第一楼”品评大会。这场大会由京城六大书院联合举办,将评出“楼宇、陈设、文化、品味”四项第一。获评者不仅得御赐金匾,更将成为京城文人雅集首选之地。
“醉仙居、邀月楼、听雨轩都收到了请柬。”林惊鸿从廊下走来,手中拿着一份名单,“据说此次评审团由翰林院五位学士、三位书画大家组成,其中首席评审,是刚致仕还乡的国子监祭酒,文渊先生。”
楚云澜展开请柬附带的规则细目,目光落在“陈设”一项:“要求参评酒楼须有‘镇楼之宝’,可为古物、字画、奇珍,需有来历、有故事、有文气。”
李管事在旁边摇头:“咱们中华楼的镇楼之宝,自然是醉翁散人的手稿和金石碑。可这些...未免太素了些。那些评审都是见惯了奇珍异宝的...”
楚云澜若有所思:“文以载道,物以传神。镇楼之宝贵在内涵,不在贵重。”她转向林惊鸿,“惊鸿,我记得你说过,文渊先生精于书画鉴赏?”
“正是。”林惊鸿点头,“他年轻时曾遍访名家,收藏甚丰,眼光极为毒辣。据说他能从一幅画的笔触、用墨、题跋中,看出作者心境乃至身世。”
“既如此,”楚云澜眼中闪过一抹亮光,“我们便以‘内涵’取胜。”
三日后,文渊阁内张灯结彩,京城十八家知名酒楼的东家齐聚一堂。主位上坐着须发皆白的文渊先生,两侧分别是其他七位评审。楚云澜与林惊鸿坐在靠前位置,旁边便是醉仙居的王富贵。
王富贵今日志得意满,见楚云澜到来,故意提高声音:“楚东家也来了?不知带了什么宝物?可别又是那些酿酒的家什,文人雅士们怕是不懂欣赏啊!”
周围传来几声低笑。楚云澜面色平静:“宝物贵在神韵,不在喧哗。王东家稍安勿躁。”
品评开始,各家酒楼依次展示镇楼之宝。
醉仙居呈上的是一尊三尺高的和田玉雕“八仙过海”,玉质温润,雕工精湛,在灯光下流光溢彩。王富贵得意洋洋地介绍:“此玉乃西域贡品,由宫廷玉匠耗时三年雕成,价值连城。”
评审们纷纷点头,文渊先生却只淡淡看了一眼,未置一词。
邀月楼展示的是一幅前朝名家吴道子的《宴饮图》,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确是珍品。听雨轩则拿出一套唐代秘色瓷酒具,釉色如春水,薄如蝉翼。
轮到中华楼时,全场目光聚焦。楚云澜缓步上前,从林惊鸿手中接过一个紫檀木长匣。匣长四尺,宽一尺,古朴无华。
她将木匣置于案上,却不急于打开,而是向文渊先生及众评审施了一礼:“中华楼的镇楼之宝,并非金银玉器,亦非名字古画。而是一幅‘无名之作’。”
“无名之作?”一位评审疑惑道,“既无名气,何以为宝?”
楚云澜打开木匣,取出卷轴徐徐展开。画作长三尺余,宽二尺,纸已泛黄,边缘有磨损痕迹。画的是月下杏林,一老者在林间独酌,笔法简淡,墨色清雅,并无落款印章。
众人仔细观看,虽觉画面意境清幽,但比起前几家炫目的珍宝,实在平平无奇。王富贵嗤笑一声:“楚东家莫非在说笑?这等画作,市井画匠一日可作十幅!”
文渊先生却忽然坐直了身子,双目微眯,紧紧盯着画卷。良久,他缓缓道:“取放大镜来。”
侍者奉上水晶放大镜。文渊先生凑近画面,细细观看每一处笔触。厅中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息等待。
一刻钟后,文渊先生抬起头,眼中精光闪烁:“此画...从何得来?”
楚云澜恭敬答道:“乃醉翁散人遗物。晚辈整理先生手稿时,在《酒经》封皮夹层中发现。”
“醉翁散人...”文渊先生喃喃重复,忽又低头细看画面一角,那里有几行蝇头小楷,因年代久远已模糊不清,“这题诗...”
楚云澜接口吟道:“‘月下独酌杏花前,一壶浊酒敬流年。丹青难写心中意,留与后人辨真诠。’”
文渊先生浑身一震,忽然老泪纵横:“是了...是了...这笔意,这诗风...是恩师的手笔!”
满座皆惊。文渊先生的恩师,乃是五十年前名满天下的“杏林居士”苏子瞻,其画作传世极少,每一幅都是国宝级珍品。
“恩师晚年隐居西山杏林,我曾多次求画,他只说‘心中有画,何必纸笔’。”文渊先生颤声道,“没想到...没想到他竟将这幅月下独酌图,留给了醉翁散人...”
他走到画前,深深一揖,转向众人:“诸位可知,此画妙在何处?”
无人应答。
文渊先生指着画面:“你们看这杏枝,七笔成枝,五笔成花,正是恩师独创的‘简笔写意法’。再看这老者衣纹,看似随意,实则暗合‘吴带当风’的神韵。最妙的是这月色——”他指向画面留白处,“未着一墨,却满纸清辉。此乃‘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最高境界。”
他越说越激动:“更难得的是,此画承载的是醉翁散人与杏林居士两位宗师的精神交流。酒道与画道,在此融为一体!”
评审们纷纷离席细观,个个叹服。王富贵面色铁青,还想争辩:“可...可这终究只是一幅画...”
“你懂什么!”文渊先生罕有地厉声道,“金银玉器,不过俗物。字画古玩,不过玩物。唯有这等承载先贤精神、传承文化道统之作,才是真正的‘宝’!”
他转向楚云澜,目光温和:“楚东家,此画你从何处悟出其价值?”
楚云澜躬身道:“晚辈最初得此画时,也曾疑惑。后反复研读醉翁散人手稿,方在一处眉批中看到:‘苏兄赠画,嘱余以酒道解画道,以画道参酒道。酒画同源,皆在写意传神。’晚辈才知,此画并非普通画作,而是两位宗师论道的见证。”
她顿了顿,继续道:“故而晚辈以为,镇楼之宝,不应是炫耀财富的器物,而应是承载酒楼精神、传承文化的载体。中华楼以酿酒传道,此画以绘画载道,正是天作之合。”
一番话说得满堂寂静,旋即爆发出热烈掌声。文渊先生连连点头:“好!说得好!酒楼酒楼,贵在文化底蕴,不在奢华陈设。中华楼有此觉悟,无愧‘天下第一楼’之名!”
品评继续进行,但结果已无悬念。中华楼一举夺得“楼宇雅致”“陈设有品”“文化深厚”三项第一,“品味独到”一项则由邀月楼获得。醉仙居虽宝物昂贵,却只得了“陈设华丽”一个次等评价。
大会结束,文渊先生特意留下楚云澜:“楚东家,老夫有一不情之请。”
“先生请讲。”
“恩师此画,可否暂借文渊阁三日?老夫想召集门下弟子,共赏先贤遗风。”文渊先生言辞恳切,“当然,老夫愿以毕生收藏的《酒经》注本相赠,其中有不少醉翁散人手迹的考据。”
楚云澜略一思索:“画作乃先贤遗泽,本应公之于众。先生既有所求,晚辈自当应允。不过——”她微微一笑,“可否请先生在画上题跋,以记今日之事?”
文渊先生大喜:“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三日后,文渊先生亲自送画归来。画卷末端已多了一篇题跋,记述品评大会始末,并盖有文渊先生鲜红的印章。更令人惊喜的是,他还带来十余位书画名家,每人在卷后空白处题诗作跋,竟将一幅三尺画卷,续成了长达丈余的“品画长卷”。
楚云澜将长卷悬于中华楼主厅,题名曰“丹青载道图”。自此,中华楼不仅以美酒闻名,更成为京城文人墨客赏画论道之地。
然而树大招风,半月后的一个雨夜,异变突生。
值夜的伙计听到主厅有异响,赶去查看时,只见“丹青载道图”不翼而飞,墙上只余空荡荡的画钩。地面有水渍脚印,直通后窗。
林惊鸿闻讯赶来,仔细勘查后沉声道:“来人武功不高,但熟悉楼内布局,应是内贼或受人指使的内应。”
楚云澜看着空墙,反而异常平静:“偷画者,必有所图。我们等便是。”
果然,次日清晨,一封匿名信投到中华楼门前。信中要求楚云澜以“九酝春”配方交换画作,交易地点定在西山荒庙,时限三日。
杜清风怒道:“定是醉仙居那帮人!师姐,我们报官吧!”
楚云澜却摇头:“画上有文渊先生及诸位名家的题跋,若闹大了,有损诸位先生清誉。况且——”她眼中闪过锐光,“我想看看,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她找来最好的装裱师傅陈老,问道:“陈师傅,若有一幅画被贼人截去一段,您能否从剩余部分看出端倪?”
陈老沉吟:“若截去的部分不大,且原画有特殊装裱工艺...或许能从撕口、纸纹中推断出被盗部分的内容。”
楚云澜眼睛一亮:“那若是在装裱时,暗中做了记号呢?”
陈老笑了:“楚东家莫非早有防备?”
原来,当初装裱“丹青载道图”时,楚云澜便留了后手。她在画心与裱绫接缝处,用特制药水写了一行小字:“此画属中华楼所有”,平时 invisible,需用特殊药水方能显现。更妙的是,她在画轴两端暗藏了机关,一旦画卷被异常移动,便会留下痕迹。
陈老仔细检查剩余画轴,忽然道:“找到了!轴头有新鲜磨损,应是盗画者匆忙间触动了机关...这磨损纹路特殊,像是某种工具所致。”
林惊鸿接过画轴细看,神色凝重:“这是‘飞爪’的痕迹。江湖上惯用此物者,多是些下三流的盗贼。”
众人顺藤摸瓜,三日内在城南贫民区找到一个绰号“泥鳅”的小贼。严加审问下,泥鳅供出是受一个蒙面人指使,报酬五十两银子,画已交到城东土地庙的神龛下。
林惊鸿带人赶到土地庙,果然在神龛下找到画卷。展开一看,画心竟被裁去一尺见方的一块——正是醉翁散人原画中老者独酌的部分。
“好狡猾!”杜清风咬牙,“他们不敢全偷,只裁走最珍贵的部分。即便我们找回剩余部分,画也已残缺。”
楚云澜却盯着那整齐的裁口,忽然道:“惊鸿,你看这裁口,如此平整,必是极锋利的裁纸刀所致。而能用这种手法裁画而不伤及裱绫的...”
“必是精通装裱之人!”林惊鸿与她异口同声。
两人对视,心中已有答案。京城中既有动机、又精通装裱的,只有一人——醉仙居的装裱师傅,孙七指。此人早年因偷盗主家字画被逐出装裱行,后投靠王富贵,专司仿制古画。
事不宜迟,林惊鸿当即带人突袭醉仙居后院的装裱坊。孙七指正在灯下对着一块画心细看,见众人闯入,慌忙将画心往怀中藏,却被林惊鸿一把夺过。
正是被裁走的那部分原画!
王富贵闻讯赶来,见状面色大变,强辩道:“这...这是我重金购得的!你们私闯民宅,还有王法吗?”
楚云澜不与他争辩,只取出一瓶药水,滴在被裁下的画心背面。片刻,一行小字显现:“此画属中华楼所有”。
铁证如山。王富贵瘫倒在地。
此事惊动了文渊先生。老人家勃然大怒,当即联合京城书画界,联名上书官府,严惩窃画之徒。醉仙居声名扫地,不日关门歇业。
画作完整归赵那日,文渊先生提议:“此画历经一劫,更显珍贵。不若举办一场‘补画雅集’,邀京城丹青妙手,共补残缺?”
楚云澜却摇头:“残缺亦是经历,何须弥补?晚辈倒有一想法——不如就以这裁口为界,左边悬挂原画残卷,右边留白,请来访者题诗作跋,记述此事。让后世之人,既赏原画风骨,亦知护画不易。”
文渊先生抚掌称妙:“好一个‘残缺亦是经历’!楚东家胸襟,不让须眉。”
于是,中华楼主厅出现了一道奇景:三尺古画悬于左,一丈白卷垂于右。中间那道整齐的裁口,像一道时间的裂隙,隔开古今,却连着同样的文化血脉。
自那以后,每日都有文人墨客前来观画题跋。白卷日渐填满,有诗、有文、有画,竟成了一卷“护画志”。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位无名氏题写的小令:
“画可裁,纸可破,文脉不可断。酒可醉,楼可倾,道统不可倾。丹青一笔非轻重,定的是天地良心,乾坤正气。”
楚云澜将这首小令裱于厅堂正中,题为“定乾坤”。
秋深了,银杏叶落满院。楚云澜与林惊鸿站在“丹青载道图”前,看那一左一右、一古一今的画卷,在烛光中相映生辉。
“惊鸿,你说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看这道裁口?”
林惊鸿握住她的手:“会看到一种精神——纵有残缺,不改其志;纵遭劫难,不灭其魂。这,才是真正的‘定乾坤’。”
窗外明月高悬,清辉洒入厅中,照在那道裁口上,竟如一道银桥,连接着古今,也连接着每一个守护文化薪火的人。
中华楼的酒香依旧,却多了一份墨香。而这份墨香,将随着“丹青载道图”的故事,代代流传,真正是——丹青一笔定乾坤,文化千载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