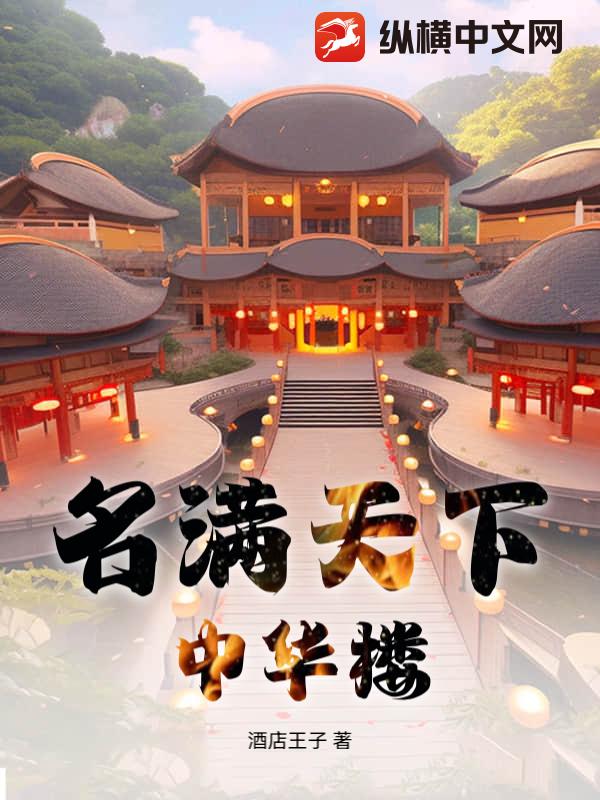正月十五,上元佳节。
京城十里长街华灯如昼,各色灯盏争奇斗艳:走马灯转着《西厢》故事,荷花灯浮在护城河上,龙灯蜿蜒穿梭人群,童子灯笑得憨态可掬。烟花不时在夜空中绽开,碎金般的光点洒落人间,映得每一张仰望的脸都熠熠生辉。
中华楼前更是灯火辉煌。楚云澜命人在楼前搭起九座灯山,取“九酝”之意。最高处一盏巨型的“醉翁灯”,以细竹为骨,素绢为面,绘着醉翁散人月下独酌的背影,灯内烛火透过绢面,将那身影映得宛如真人。
林惊鸿陪着楚云澜站在三楼廊上,俯瞰楼下盛景。她今日穿着月白色衣裙,外罩浅碧披风,发间只簪一支白玉簪,简素得与满城繁华格格不入,却又自有种清冷气度,让人在万千灯火中一眼就能看见。
“今年灯市比往年更热闹三分。”林惊鸿轻声道。
楚云澜微笑:“百姓需要这样的热闹。去年北疆雪灾,江南水患,朝廷虽尽力赈济,终是苦了百姓。能有个佳节忘却烦忧,也是好事。”
她说着,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东南方向——那是楚家旧宅所在。十五年前的那个上元夜,楚家也曾张灯结彩,母亲亲手做的兔子灯挂满回廊,父亲抱着六岁的云舒猜灯谜……
“又在想云舒?”林惊鸿握住她微凉的手。
楚云澜轻轻点头:“去年今日,她传信说‘冰雪消融日,姐妹重逢时’。如今一年过去,冰雪又融,却仍无消息。”
这半年多来,幽冥教在江湖上销声匿迹。有人说新任教主铁腕整顿,已将教中势力化整为零;也有人说幽冥教早已解散,余党各奔东西。可楚云舒的下落,却成了一道无人能解的谜。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欢呼。两人循声望去,见醉翁灯下,杜清风正带着醉翁学堂的学徒们表演“酒令灯谜”。学徒们各执一盏特制的酒壶灯,壶身上写着谜面,壶嘴处垂下纸条写着谜底,猜中者可取下一张,集齐九张可换一坛“九酝春”。
一个青衣学徒朗声道:“此谜题曰——‘清泉石上流,明月松间照。酿得乾坤液,醉倒南山老。’打一酿酒工序!”
人群中议论纷纷。一个老酒客沉吟道:“可是‘汲水’?”
“非也!”学徒笑着摇头。
另一个年轻书生猜:“是‘蒸粮’?”
“亦非正解。”
正当众人苦思时,一个清越的女声从人群后传来:“可是‘凝露’?”
人群分开,只见一位身着淡紫衣裙的女子盈盈走来,面覆轻纱,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她走到灯前,继续道:“清泉明月喻水之纯净,乾坤液指酒,南山老指醉翁。酿酒首重水质,需取晨间花木之露,是为‘凝露’。”
学徒击掌赞叹:“姑娘高才!正是‘凝露’!”说着取下谜底纸条递上。
紫衣女子接过,却不离开,反而抬头望向三楼。虽然隔着面纱,楚云澜却分明感觉到,那目光直直落在自己身上。
她的心猛地一跳。
女子又连猜八谜,句句切中肯綮,对酿酒工序的了解竟不逊于学堂学徒。当她取齐九张纸条时,全场掌声雷动。
杜清风亲自捧上一坛“九酝春”:“姑娘真乃知酒之人。敢问芳名?”
女子微微一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上三楼:“我姓楚。”
楚云澜浑身一震,抓着栏杆的手指微微发白。林惊鸿也神色一凛,低声道:“我去请她上来。”
“不,”楚云澜稳住心神,“我自己去。”
她转身下楼,脚步看似从容,心中却翻江倒海。是她吗?真的是云舒吗?为何选在今日现身?又为何蒙面而来?
走到院中时,紫衣女子已抱着酒坛站在杏树下。落尽叶子的枝桠上挂满了小巧的莲花灯,暖黄的光晕映着她单薄的身影,竟有几分萧索。
四目相对,一时无言。
最后还是紫衣女子先开口:“姐姐不请我喝杯茶吗?”
声音虽然沙哑,却的的确确是楚云舒的嗓音。
楚云澜鼻尖一酸,强忍住泪水:“楼上请。”
三楼雅室,烛火通明。楚云舒终于摘下面纱——还是那张清丽的脸,却瘦了许多,眼下有淡淡的青影,仿佛许久未曾安眠。最让楚云澜心痛的是,妹妹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天真烂漫的六岁女童,也不是三个月前那个满眼仇恨的幽冥教主,而是一种极深的疲惫,和一丝难以察觉的释然。
“云舒……”楚云澜千言万语堵在喉间,只化作这一声轻唤。
楚云舒笑了,笑容里有泪光:“姐姐,我回来了。”
林惊鸿悄然退出,掩上门,将空间留给姐妹二人。
楚云舒从怀中取出一枚令牌,放在桌上——正是幽冥教主令。
“三个月前,我回到总坛,召集所有教众。”她声音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说,幽冥教作恶太多,该结束了。愿意改过自新的,我赠予银两,助其安家立业;执迷不悟的,我便亲手清理门户。”
楚云澜握住她的手:“你受苦了。”
“比起姐姐这十五年受的苦,我这三个月不算什么。”楚云舒反握住姐姐的手,掌心有薄茧,是常年握剑留下的,“最难的不是对付那些顽固之徒,而是面对自己——面对这双手曾经沾染的无辜鲜血。”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有一个分坛主,曾为夺一户人家的传家宝,杀其全家七口,连三岁幼童都未放过。我杀他时,他笑说:‘教主,您手上的人命可不比我少。’”
楚云澜心中一痛。
“他说得对。”楚云舒泪如雨下,“这些年在养父的蒙骗下,我杀了多少人?那些人或许有罪,或许无辜,可我都未曾查证,只因养父一句‘他们是仇人’,便挥剑相向……姐姐,这样的我,还配做楚家的女儿吗?”
楚云澜将她拥入怀中:“傻丫头,你那时年幼,受人蒙蔽,岂是你的错?你能迷途知返,清理门户,已是莫大的勇气。父亲母亲在天有灵,只会为你骄傲。”
姐妹俩相拥而泣,十五年的分离、误解、伤痛,都在泪水中渐渐融化。
良久,楚云舒擦干眼泪,正色道:“姐姐,我今日来,除了与你相认,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她从怀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册子:“这是我从养父密室中找到的。他临终前说,这册子里的秘密,足以动摇半个朝堂。”
楚云澜接过,翻开一看,神色渐渐凝重。册子里记载的,竟是十五年前幽王谋反案的真相——以及一桩牵连更广的阴谋。
原来当年幽王谋反,背后另有主使。那人利用幽王囤积军械,实则打算在幽王起事时,以“平叛”为名调动大军,行“清君侧”之实,夺取皇位。而楚林两家之所以遭难,正是因为楚啸天查到了蛛丝马迹,林镇岳则是因为拒绝参与兵变。
“养父便是那人的心腹之一。”楚云舒道,“他奉命灭口楚家,嫁祸林家,一箭双雕。后来那人登基无望,便隐于幕后,养父则创立幽冥教,继续为其效力。”
楚云澜握紧册子:“那人是谁?”
楚云舒摇头:“养父至死未说真名,只以‘烛龙’称之。但册中记载了几次密会的地点,其中一处……姐姐一定熟悉。”
她指着一行字:“天佑七年上元夜,城南旧茶坊。”
楚云澜如遭雷击。城南旧茶坊,正是当年楚家遇害前,父亲最后出门去的地方!母亲曾说,那夜父亲接到一封信,说是故人有约,便匆匆出门,再回来时面色凝重,深夜还在书房写信。第二日,楚家便遭灭门。
“烛龙……烛龙……”楚云澜喃喃道,“‘幽王案’后,先帝曾做一梦,见烛龙衔珠照夜,醒后以为吉兆。难道……”
她不敢想下去。若真如猜测,那这桩阴谋牵扯之深,恐怕远超想象。
门外忽然传来三声轻叩,是林惊鸿与杜清风回来了。楚云澜忙将册子收起。
四人围坐,楚云舒将幽冥教之事简单说了,隐去了“烛龙”一节。杜清风听罢,长叹一声:“楚姑娘能拨乱反正,实乃大义。只是幽冥教虽散,江湖上却新起了一股势力,名唤‘暗香阁’,行事诡秘,专与各大商号为敌。这几月,已有三家酒楼被其逼得关门。”
林惊鸿皱眉:“我也听说了。据说暗香阁擅用香料,能在不知不觉间令人神智昏沉,任其摆布。”
楚云舒神色一动:“香料?幽冥教也曾用此手段。有一种‘迷魂香’,无色无味,混入酒中,饮者如坠幻梦,问什么答什么。”
楚云澜心中一惊,忽然想起一事:“三个月前,醉仙居王富贵曾想买‘九酝春’配方不成,后来便再未来纠缠。我原以为他死心了,现在想来,或许……”
话未说完,楼下忽然传来一阵骚动。李管事慌张上楼:“东家,不好了!有客人饮酒后突然发狂,砸了好些器物!”
四人急忙下楼。只见大堂中,一个锦衣男子双目赤红,正挥舞着板凳乱砸,口中胡言乱语:“我是皇上!你们都要跪我!哈哈!我是皇上!”
周围客人吓得四散,几个伙计想上前制止,却被他力大无穷地甩开。
楚云舒一眼看出端倪:“他中了迷魂香!药性太猛,神智已失!”
林惊鸿身形一闪,已到那人身后,一记手刀精准劈在其颈侧。男子软软倒下,被伙计扶住。
楚云澜上前查看,嗅到男子口中一股极淡的异香。她面色凝重:“是我们楼里的酒。”
她立刻命人封存今日所有酒坛,一一查验。一个时辰后,结果出来——有三坛“金桂香”被动了手脚,掺入了迷魂香。
“下药之人对酒楼很熟悉。”杜清风分析,“知道酒窖看守的换班时辰,也能避开伙计耳目。”
楚云澜忽然想起什么,问李管事:“今日可有生面孔进过后厨?”
李管事思索道:“除了送菜的老王,就只有……对了!午后醉仙居派人送了一盒点心,说是给东家赔礼。送点心的小厮说想看看咱们的新灶台,我便让他在后厨转了转。”
一切明了。醉仙居与暗香阁,恐怕早有勾结。
楚云舒冷声道:“姐姐,此事交给我。幽冥教虽散,但我还有些人脉,能查到暗香阁的底细。”
楚云澜摇头:“太危险。你既已脱身,不要再卷入江湖纷争。”
“可他们欺到姐姐头上了!”楚云舒握住她的手,“姐姐,让我为你做点什么。这十五年,我未曾尽过妹妹的本分,如今终于有机会……”
楚云澜看着她眼中的恳切,终是点了头:“好,但你要答应我,凡事以安全为重,不可涉险。”
当夜,楚云舒悄然离去。楚云澜站在楼前,望着她消失的方向,久久不语。
林惊鸿为她披上外衣:“放心,云舒今非昔比,她能保护好自己。”
“我知道。”楚云澜轻叹,“我只是心疼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却经历了这么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林惊鸿望向满城灯火,“你看这万家烛火,每一盏下都有悲欢离合。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自己这一盏,或许还能照亮旁人。”
楚云澜心中一动,忽然明白了他话中深意。
她转身回楼,取出那本册子,在灯下细看。烛火摇曳,将字迹映得忽明忽暗。那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阴谋、背叛、杀戮,此刻都化作纸上的墨迹,沉默地诉说着过往。
但她知道,沉默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有些公道,必须讨还。
“惊鸿,”她抬起头,眼中燃起坚定的光,“我要查清‘烛龙’的真实身份。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还父亲、还楚林两家、还所有被卷入之人的清白。”
林惊鸿在她对面坐下:“我陪你。”
四手相握,掌心温暖。
窗外,上元灯火渐次熄灭,长街从喧嚣归于寂静。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东方已现鱼肚白。
楚云澜吹灭烛火,晨光透窗而入,照亮室内的每一寸角落。那些在黑暗中显得狰狞的秘密,在光线下,也不过是泛黄的纸张、褪色的墨迹。
“天亮了。”她轻声道。
林惊鸿推开窗,清冷的晨风涌进来,带着冰雪初融的气息。楼下已有早起的小贩开始摆摊,热腾腾的蒸汽升腾而起,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楚云澜走到窗边,与他并肩而立。远处钟楼传来悠长的钟声,一声又一声,回荡在苏醒的京城上空。
灯火阑珊处,她看清了自己的本心——不是沉溺于过往的伤痛,不是畏惧于前路的艰险,而是坚定地走该走的路,守护该守护的人,澄清该澄清的真相。
这条路或许漫长,或许坎坷,但她不再孤单。
晨光中,中华楼的匾额熠熠生辉。而楼中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